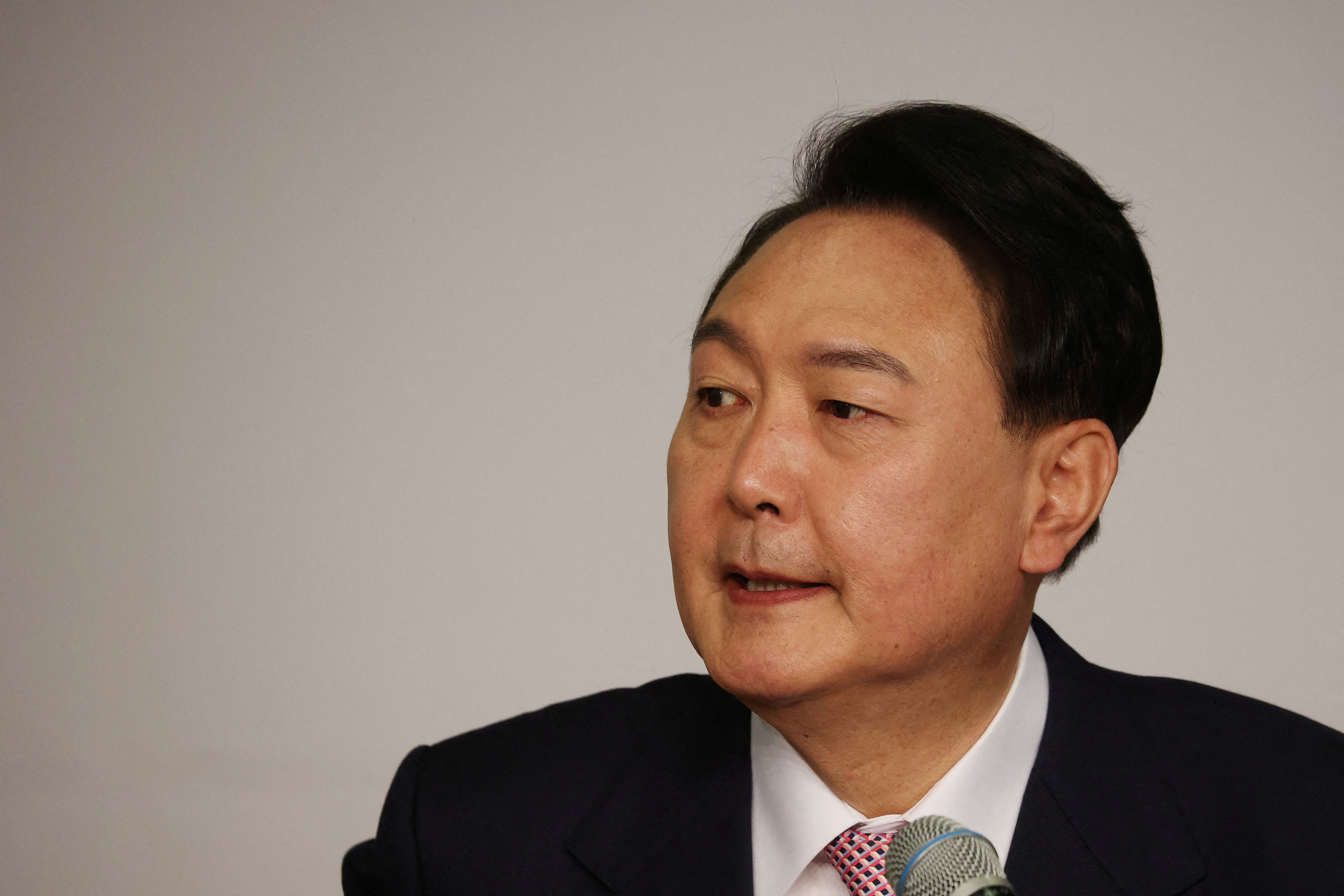尼泊尔女性的经期恶梦 被迫住在粗陋的「月经屋」承受强暴、蛇咬风险
-

示意图,传统尼泊尔女性。(取自hippopx图库)(photo:UpMedia)菈妲(Radha)的晚餐七点会送过来。她在草棚后面蹲下来,这里离家里有一段距离,她只能等待。菜色她都会背了:前天是白米饭,昨天是白米饭,今天也是白米饭,而送饭来的肯定是妹妹,手举得高高的,把饭扔到盘子里,像餵狗那样。
在尼泊尔西部的佳木(Jamu),菈妲的地位低人一等,她出身锻工阶级,属于贱民。每次月经来潮,她的地位又再低一阶,虽然才十六岁,但行经期间不准进家门、不准吃东西(白米饭除外)、不准碰其他女性,就连奶奶、妹妹都不行,一碰就脏。如果碰了男子(或男童),那人就会浑身颤抖、反胃生病,如果吃到奶油、喝到牛奶,那牛就会生病挤不出奶。如果进到寺庙、膜拜神明,神明就会震怒降灾、派蛇咬人作为报复。但菈妲可以上学,很多女生却连上学都不准。
在菈妲的村子里,月经是秽物,行经的女孩容易招厄,因此人见人怕、能躲则躲。

*(photo:UpMedia)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Pixabay)
月经女屋
晚餐后,菈妲准备就寝。佳木这里没有电,黄昏后天黑得很快,村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维持着古老的生活节奏。菈妲的父母都不在,佳木当地的男人大多到外地工作去了,尼泊尔很多地方都人口外流,有些女性(例如菈妲的母亲)也到外地讨生活。在印度,尼泊尔人是称职的保全;在波斯湾,尼泊尔人是建筑工人,而且常常是在体育场或从鹰架上摔死的建筑工人。菈妲跟奶奶、妹妹同住,一屋子都是女生,屋里有太阳能照明灯,对面人家里也有,我就住在菈妲对面,同行的还有两位旅伴,一位是安妮塔(Anita),她是尼泊尔水援组织(WaterAid Nepal)通讯暨性平官,另一位是摄影师帛璐美(Poulomi),接待我们的女主人是佳木当地的老师,看起来人很好。
菈妲这星期用不到太阳能照明灯,因为她要在外面过夜。她带我走过「大马路」,上头铺着大大小小的石头,这就算是路了,只适合摩托车、行人、蛇通行。我们爬上陡峭的山丘,穿过高高的草丛,来到一间矮小的棚屋,看起来像给牲口住的,但比牲栏更窄小、更简陋,墙板搭建得很随便,房顶也没铺好,菈妲必须睡在这里,因为她月经来了。
用当地的话来说,菈妲是「chau」了,这个字源自尼泊尔远西省(Sudurpashchim Pradesh)阿查姆地区(Achham)拉乌特族语,意思是「月经」,后来引申指「月经来的低贱女子」,英文的「taboo」也是同样的词义引申,最初源自玻里尼西亚语的「tapua」(月经)或「tabu」(隔离),后来引申指「禁忌」,而隔离生理期女子就叫做「chaupadi」(padi意指「女子」),「棚屋」则是「goth」,不管叫「chaupadi goth」还是「月经女屋」,菈妲都讨厌,「我被逼着在这里过夜。爸妈不让我住家里。我不喜欢这里,很黑,没有灯,冬天很冷,我很害怕」。
强暴事件层出不穷
菈妲冬天睡在这间有墙板的矮小棚屋里,里头低矮到只能用爬的,夏天则睡泥土地,底下是一百二十公分见方的平台,四面通风,上头盖着一片茅草屋顶。月经女屋里连一个人睡都嫌窄,今晚却要睡三个人。菈妲的亲戚嘉穆娜(Jamuna)月经也来了,她把一岁的儿子带来跟菈妲一起睡。菈妲很感谢嘉穆娜来作伴,这样或许可以帮忙挡一挡醉汉,醉汉如果想要逞兽欲,忘记经期女性碰不得的禁忌就可以了,再方便不过,女人家也不敢说什么,怕玷污了自己的名声。可是,月经女屋里的强暴事件层出不穷,遥远的加德满都报纸上偶尔会报导,当地女性被问起都会低下头或别开视线。
除了强暴之外,被蛇攻击或被蛇咬死的事件也时有所闻(我才在佳木待了三天,就看到三条蛇,而且是大蛇)。二○一六年十二月初,十五岁的洛希妮.迪鲁瓦(Roshani Tiruwa)在月经女屋里点火取暖,结果窒息身亡。二○一七年夏天,尼泊尔西部代莱克区(Dailekh)的杜菈曦.夏伊(Tulasi Shahi)经期间住在叔叔的牛棚里,结果被蛇咬死。
菈妲家族的月经女屋有时会睡四到五位女性,简直多到难以想像,要睡在其他地方也是可以,但都比不上家里安全又温暖。越深入尼泊尔高原,我越难相信自己的眼睛:一位十四岁少女带我去看她准备如何过夜,先是在家门外的土地上搭起蚊帐,把蚊帐的四个角绑在木桩上,一躺进去鼻尖就快顶到帐顶,就这样睡在泥土和玉米壳上,用垃圾做床。她月经才来第三次,就已经学会认命。不然怎么办呢?
佳木地处偏远。我们从加德满都搭乘佛陀航空,两个小时之后降落在尼泊尔根杰(Nepalgunj),航程期间一名老妇人要求开窗,说是要吐痰,然后—谢天谢地,窗户打不开—一路吐到目的地,对着袋子「卡……呸」,吐得不亦乐乎,看得我两眼发直,听得我心惊胆颤。出了尼泊尔根杰的机场,我们开了四个小时的车,一路上坑坑洞洞,只有几段(心血来潮)铺了柏油,安妮塔不时要下车搬大石头搭桥,好让我们的吉普车驶过意料之外的洪流。
最后,我们连同行李一起被丢包在河边,电子产品全用塑胶制品包起来,确定安全无虞之后才涉水过河,这里虽然水深及股,却是唯一通往佳木的路。我们来到尼泊尔的中西部,但不是在喜马拉雅山一带,四周并非嶙峋陡峭的山岳,而是蓊郁苍翠的山丘,这里是我到过最美丽的地方,但我却是来探访最丑恶的事件。

*(photo:UpMedia)美丽的尼泊尔。(Pixabay)
女人自己为难自己
根据二○一○年官方调查报告:尼泊尔西部的妇女,五八%必须在生理期间住月经女屋,4由于佳木位在尼泊尔中西部的山丘,因此官方判定当地妇女遭受严重歧视(住棚舍、独食)的比率低于一○%,5我也以为佳木民风开化,毕竟地势比较低、交流比较容易,平等、解放的观念比较容易进来(但要用走的,开车到不了),妇女不该因生理机制被流放到无法供暖的棚舍。因此,我很担心(这种挖新闻的心态真该死)月经女屋已经成为历史。
又渡了三条河,再步行一个钟头,我们抵达纳西村(Narci),还要再过几座村庄才会到达佳木。我们经过的第一间房子外头就有月经女屋,第二间房子外头也有,沿途的每一间房子外头都有,要不是二○一○年的调查人员不喜欢渡河,就是当地居民没说实话。有些月经女屋里头摆放着私人用品,例如一把梳子(插在茅草屋顶上)、一瓶红色指甲油,有些摆放着教科书,女孩(在学校跟男生平安共处,没害人生病、没酿成灾祸)放学回来可以读书。经期隔离的种种限制虽然严格,上学一事倒是可以通融。纳西村的牛棚、谷仓都很整洁,还晾着玉米壳,准备冬天做饲料,地上也扫得很干净,月经女屋却没人整理,因为太小了,想扫也没办法扫。
一群女人聚在一起就是要聊天,其中一位村妇问:坐在哪里好?我们走向正屋前那排台阶,走上去就是一楼,村妇见状阻止我们:「我不行。我第五天。」
我们改坐在屋前的空地上,全都是女的,三个外地来的拿着笔记本问东问西,村民很有耐心地坐着,好心好意要回答问题。一位村妇手持镰刀,名叫楠妲卡菈(Nandakala),正好月经来,她同意其他村妇说的—经期就是要隔离,如果月经来了却不守禁忌,坏事就会降临:牛上树,男人发抖、生病,蛇循着罪孽而来。另一位村妇听了很激动,说:「对,真的。一条大蛇跑到我家来了。大家都看到了。」另一位村妇则说:「如果碰了东西,我自己会生病,所以隔离就隔离,有什么难的呢?」经期隔离可以保大家平安,一起围坐的村妇中,没有半个人抗议。「这是传统,」她们异口同声,「我们上一辈这么做,上上一辈也这么做,所以我们也照着做。」我问如果有人说经期隔离是不对的,她们会怎么回答?会承认自己支持经期隔离吗?「我们会老实回答。会把刚刚跟妳说的话再说一遍。」
楠妲卡菈带我们到一百公尺外的月经女屋拍照,在这里她说话坦率多了。她不担心被强暴。男人都到印度或杜拜工作了,哪来的强暴犯呢?她跟帛璐美说:「我当然讨厌月经女屋。」冬天很冷,夏天很热,限制那么多,令人透不过气,真不公平。「为什么神要处罚我们?为什么女人活该要受罚?但我们又能怎么办?」
到了下一座村庄,我们在一户人家过夜,窗外是湍急的贝里河(Bheri River),湛蓝而不羁。村里房舍簇集,九成屋外都有月经女屋,其中一间月经女屋里摆着一副杯碗,到访的女客才刚刚离开,依照习俗在月经女屋里住了六天,过火净身后才进家门,这位住了六天的女客是一位未婚少女,已婚妇女不需要住满五天或六天,只需要住三天即可。接待我们的女主人说:「我不相信这一套,但我婆婆深信不疑。」
经期隔离并非父权社会套在受难妇女身上的邪恶枷锁,而是女人自己为难自己,从奶奶、婆婆到妈妈,一代一代承袭下来。楠妲卡菈私底下胆子很大,之前随丈夫到孟买住了六年,期间并未遵守月经隔离的禁忌,丈夫因此生病,眼睛痛、膝盖痛、全身抖。「都是我害的,」楠妲卡菈说,「这禁忌虽然不对,但该守的还是要守。」现在她每个月都到月经女屋报到。
接着到了下一座村庄,一位月经来的女学生跟我们交谈,我们之所以知道她月经来,是因为她不肯靠近我们。女学生说:「我不准进家门、不准碰水、不准碰男人。」但家事还是得做,买东西也还是她去跑腿。「我必须跟店家说我月经来,店家就用丢的把东西丢给我。」有时候不用说,只要表现出不肯从店家手中接过东西的样子,店家就懂了。她在学校碰过男同学,但什么事也没发生。「月经当然很脏,」女学生说,她坐在月经女屋里,手边摆着课本,但这书里怎么就没教她月经一点也不脏呢?「月经是秽物。」
※本文摘取自《九品脱:打开血液的九个神祕盒子,探索生命的未解之谜与无限可能》,联经出版。

*(photo:UpMedia)作者简介
萝丝.乔治 Rose George
牛津大学现代语言学士、宾州大学国际关系硕士,身兼记者和作家,洞见症结,深入探讨不易查晓的重要议题,向来以对无形却至关紧要的主题所从事的无畏研究而着称。
处女作《流离失所》(A Life Removed)追踪报导赖比瑞亚难民的生活,成名作《厕所之书》(The Big Necessity: The Unmentionable World of Human Waste and Why It Matters)探讨排污系统与卫生的关联,《冰山之下》(Ninety Percent of Everything)则从海运业切入带出全球化议题。也为《纽约时报》、《金融时报》、《页岩》(Slate)以及其他出版品撰稿。目前定居于英国约克郡。
译者简介
张绮容
中华民国笔会会员,台湾大学外文系学士,台湾师范大学翻译研究所博士,现任东吴大学英文学系助理教授,译作包括《死亡赋格:西洋经典悼亡诗选》、《教你读懂文学的27堂课》、《傲慢与偏见》、《大亨小传》等二十余本,热爱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