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官员的疑问:为什么蒙古人不放弃落后的母语,改说「文明」的汉语呢?
-

着传统服装、站在蒙古包前的蒙古人。(取自世界银行)(photo:UpMedia)在这次的调查中,我遇见形形色色的穆斯林。他们跟我陈述教团殉教的历史,以及社会主义时代的苦难。殉教和苦难是他们在生活中,记忆最深刻的部分。若是不了解这种生活方式,历史叙述就毫无意义。有一句座右铭说,「历史叙述就是对事实的探究」。对事实的探究固然永无止尽,但最终仍然要归结到生活方式上,而描述这些事实的我,又能贴近他们的心灵到什么地步呢?
我自己也是中国少数民族的一员;因此,在以同等的少数民族为对象、进行调查研究时,绝不能刻意偏袒某一方,或对另一方大加批判。西北地区的回族、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几乎所有少数民族,各自都有一段殉教历史。张承志将神祕主义教团哲合忍耶派的殉教历史,写成一部心灵史——当然,他也不是全然无视其他教团的殉教史。对于回族和撒拉族的关系,我们往往得透过他们和其他民族间具有能动性的关联,方能捕捉其历史。同样身为少数民族,我希望至少能好好把这些人的生活方式传达出来,这就是我的目的之一。
另一方面,透过对他者、对其他少数民族的研究,也可以重新认知自己所身处的状况。透过这次和保安族、东乡族、回族人们的交流,我得以从别的角度,对居住在内蒙古自治区内蒙古族人的立场,以及蒙古文化的递嬗,进行重新的思索与认知。
对少数民族统治的刚与柔
中国四千年历史中,对外交涉的历史主要部分,对应的就是北方游牧民族的历史。结果,汉族从这段历史中学到很多东西。即使在近现代,汉族对列强的外交堪称无能透顶,但对周遭各民族的交涉,倒还颇能掌握诀窍。
在现代中国民间,有一段表现如何顺畅统治少数民族的俗谚:
这实在是相当狡狯的统治理论。就像「下马的蒙古人就不算蒙古人」这句蒙古谚语说的一样,住在现今内蒙古自治区内、过着定居生活的蒙古人,完全失去了向中国积极提出自己主张的意愿与活力。可是,光是保障宗教与商业的自由,是绝对无法让藏人与回民感到满足的。

*(photo:UpMedia)竖立在北京市中心天安门广场西侧的宣传看板。(八旗文化提供)
看板上描绘了五十五个少数民族;其中劳工、农民、知识分子和解放军士兵,全都是汉人。汉人士兵左侧的维吾尔女性拿着水果,表示是绿洲的居民,至于蒙古人和藏人,则拿着和游牧全无关系的花束。
中国共产党对各少数民族的统治,总是採取软硬兼施的手段。
有一件相当奇妙的事:在内蒙古自治区,由政府主导执笔出版,展现社会主义成果的地方志,完全不准邮寄到国外,就连申请国际标准书号(ISBN)也不行。我问邮局人员理由究竟为何,他们说「这是为了防止向外国传递不正确的资讯」。一副责任感强烈的模样;看来,内蒙古自治区的政府干部似乎相当担心,「不正确的资讯」流到外国,会让外国研究者据此写下「不正确的论述」。但是,只要跨出内蒙古自治区的边界一步,不管什么的地方志都可以邮寄;隔壁的陕西省也好、北京也好,也是如此。
几年前,我和日本的某个学术调查团一起造访了内蒙古自治区的巴林右旗,由我担任团长的通译。当地共产党书记为我们举办了欢迎晚宴;席间有蒙古人,也有汉人,因此我将团长的日语演说按顺序,先翻成蒙古语再翻成汉语。
但是,我此举让汉人书记相当不满。在干杯之后,只见他迅速地站起身,对我说:「翻译的时候要先翻成汉语,然后才翻成蒙古语!」从北京一起同来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蒙古籍研究者也劝我说,「要稍微现实一点!」会场的气氛一下子降到冰点,但我的内心却熊熊燃烧起来。在内蒙古自治区,公用语应该是被认定为「主体民族」(非多数者!)的蒙古族母语,巴林右旗的共产党书记却忘了这点——不,汉人干部其实应该是打从心底觉得很不可思议,为什么蒙古人不放弃自己落后的母语,改说「文明」的汉语呢?
在软硬兼施方面,内蒙古自治区的统治较倾向哪一边呢?答案应该算是「软」的一面。虽然偶尔会有政府把不经许可创设研究会的知识分子、或是组成乐团的年轻人逮捕入狱的情况,不过像对伊斯兰哲合忍耶派领袖发动的强权镇压,倒是相对少见。可是,在内蒙古自治区,有另外一种肉眼看不见的压力。在企业与政府机构内,只要稍微敢主张一点蒙古族的权益,恐怕就得面临到升迁无望、被赶出重要位置的命运。因为直接逮捕会遭到外国批评「压抑人权」,但对于这种巧妙的手段,要监视是有其难度。特别是地方干部为了避免在自己任内出现问题,于是会推行自我阉割、防范未然的政策。
因此,即使中央政府没有下令禁止地方志寄送到外国,他们也会凭着自己的判断下达禁令。与其等到问题发生——说实话,地方志究竟会产生什么「问题」,我还真是想不出来——被追究责任,他们的想法是,还不如先下手为强。面对这种巧妙的手段,有一部分蒙古人还主张「要现实一点」;这些准变节者的存在,更导致自治区内的少数民族人民,自我放弃本来应该确保的权益。

*(photo:UpMedia)竖立在北京市中心天安门广场西侧的宣传看板。(八旗文化提供)
贞操与汉化之间
这是张承志名着《黑骏马》终章中的一幕。这是主角之一「我」过了好几年后,拜访过去的恋人;在我们再度告别时,她跟「我」所说出的话。曾是恋人的她,在「我」离开的这几年间,在不可抗力的情况下,跟草原上的某个小混混怀孕生了孩子。但是,她和所有蒙古人一样,把生下来的女儿当成是一条宝贵的性命在养育。就像她一直没有忘记「我」一样,她生养的女儿也把「我」当成是真正的「父亲」——一位宛如蒙古古老民谣描述般,骑着黑色骏马的「父亲」。
张承志所描绘的,正是蒙古人的生命观。没有比生命更重要的事物;不管家畜也好、人也好,大家都是一体的。游牧民的小帐蓬平时是人的栖身之所,但在寒冷时,也会让孱弱的家畜入内避难,一切都是为了守护生命。家畜和人是同等重要的存在;无数的蒙古民间传说和故事都在讲述这一点。而张承志只是把其中一则古老故事,编织进自己的小说。
可是,内蒙古自治区的优雅文人、以及难以取悦的评论家,并不喜欢张承志的《黑骏马》,反而对它勐烈抨击。他们的理由是:「蒙古女人最重视贞操了,怎么可能这么简单生下别人的孩子、养育别人的孩子呢!」。
这完全是胡说八道。在历史上,北亚游牧民一直抱持和中华世界迥异的价值观。对草原民族来说,中华儒家高唱的理念,不只伪善而且毫无用处。所以当和外部世界自由交流的时候,他们选择西方的波斯文明与印藏文明,来显示自己与中华世界的异质性,并保持自己的认同。随便拿起一本编年史就可以看见,直到十八世纪为止,蒙古的知识分子都主张,成吉思汗王家是和印藏密切相连,跟中华的三皇五帝则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认为那些抱持草原女性会有「儒教的贞操观」,这种空想的现代内蒙古自治区文人,他们完全缺乏和外部世界的交流,才会产生这种毫无道理的认知。更准确来说,他们比回族的张承志,汉化得更厉害。甚至他们会主张,「草原的女性都跟嫁给匈奴的王昭君,学来了缠足的习惯」。
在文化大革命史无前例严酷的政治环境中,从大都会北京被下放到草原的青年张承志,受到草原老妇人温柔的对待,也一直把她当成母亲尊敬。在他的着作中写到,「我有两个母亲」;他回顾起来,认为自己和母亲的关系,绝非社会学与人类学概念能轻易表现。
虽然是比较单纯的说法,回族出身的张承志对蒙古有一份特别的爱。他对蒙古的爱,也对我的伊斯兰社会调查研究,产生很大的影响。当我受到它的刺激、反覆思量之际,总有一种叛逆的快感油然而生。
※本书摘取自《蒙古与伊斯兰中国:一段贴近民族心灵的旅程》,八旗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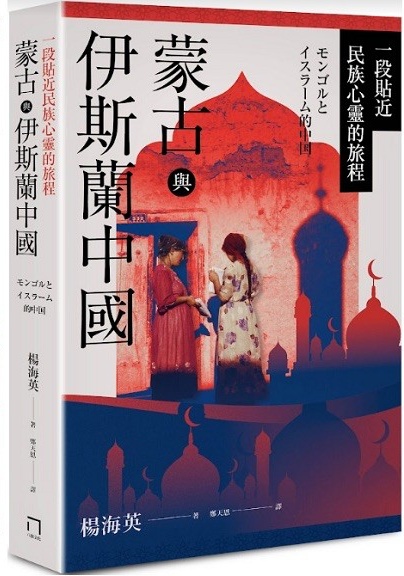
*(photo:UpMedia)作者简介
杨海英
蒙古裔文化人类学家。蒙古名「俄尼斯.朝格图」,蒙译日文名「大野旭」。1964年生于内蒙古自治区的鄂尔多斯,毕业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大学日本语系,1989年赴日本留学,修完国立民族学博物馆综合研究大学院的博士课程而获博士(文字)学位,现为日本静冈大学教授。自1993年到2019年,每年都到内蒙古进行研究。
曾获司马辽太郎大奖(第14回,2010年)、大同生命地域研究奖励赏(2015年)、樫山纯三赏(2015年)、正论新风赏(第19回,2018年)。
繁体中文版作品有:《没有墓碑的草原》(八旗文化,2014年)、《蒙古骑兵在西藏挥舞日本刀:蒙藏民族的时代悲剧》(大块文化,2017年)、《在中国与蒙古的夹缝之间:一个蒙古人未竟的民族自决之梦》(八旗文化,2018年)、《文明的游牧史观》(八旗文化,2019年)。
译者简介
郑天恩
台湾大学历史所硕士,曾任出版社日文编辑,现为专职翻译。译有《何谓中华、何谓汉》、《曾经以为中国最幸福》、《人民解放军的真相》、《凯尔特.最初的欧洲》、《文明的游牧史观》(以上由八旗文化出版)、《海上霸权》、《日本人的界限》(合译)、《东方直布罗陀争霸战》、《珍珠港》、《最后的帝国军人》等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