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势已去到新的探索:藏在栗子里的供销社过往 | 专访
-

2023年1月20日,吉林,一家大型商场内设置的供销社,玉米粮大囤。2023年1月20日,吉林,一家大型商场内设置的供销社,玉米粮大囤。(photo:JieMian)记者 | 潘文捷编辑 | 黄月
1996年,谁也没有想到,有着“政府背景”、垄断了当地商品流通业务近40年的河北省小豆庄供销社(注:小豆庄为匿名),因为板栗业务的失败,导致多个基层供销社和数百位栗农蒙受了高达500万元的损失。这件事成为了当地供销社大势已去的一个标志。
北京城市学院副教授张文潇就来自小豆庄,从一颗小小的栗子入手,她试图厘清包括供销社在内的中国农产品流通体系转型。她在《栗子的故事》一书中写道:“500万亏损案发生后,供销社通过各种方式残喘了八年,长时间的内耗,加之难以与诸多市场主体竞争,供销社在当地的权威形象逐渐被打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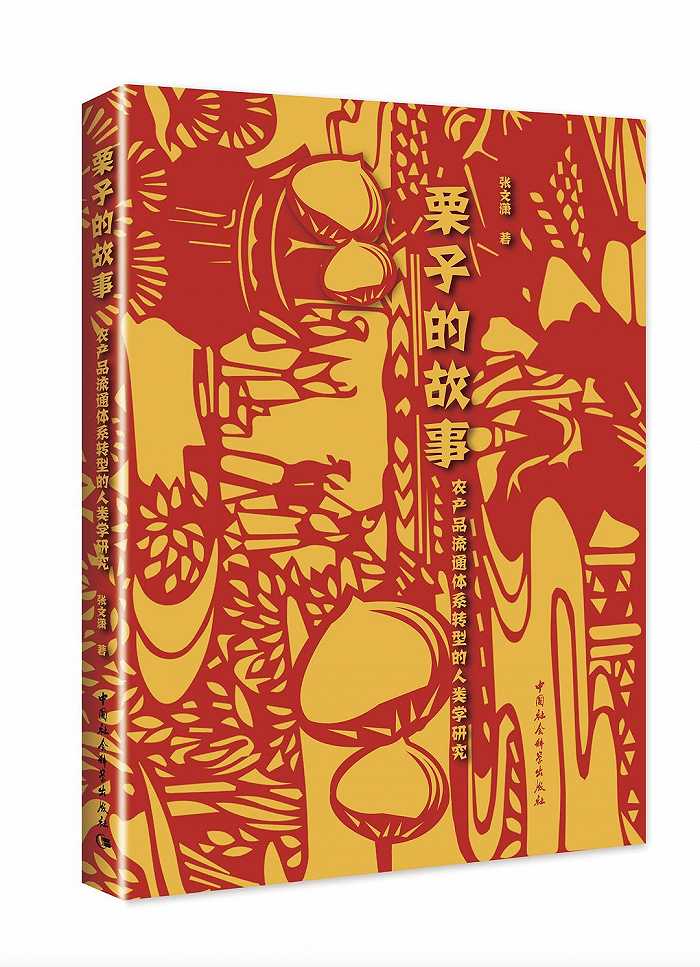
*(photo:JieMian)在张文潇笔下,供销社是这样一个组织,它是不隶属于国家机构的自主联合体,但其功能包括为国有贸易公司收购土产以及销售外来品。在此基础上,两者共同致力于农村贸易的社会主义化。
供销社在不同时期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在社会主义改造期间,从“供”的角度看,供销社管控了农村的消费领域,几乎杜绝了自由买卖的可能;从“销”的角度看,通过对重要农产品和其他物资的计划收购和统一收购,供销社帮助国家实现物资的流通。张文潇看到,这一时期,供销社主要发挥了从乡村汲取资源的作用,助力“以农辅工”。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基层供销社体系面临着诸多挑战,全国各地的许多供销社经历了日渐式微的过程,“但是供销社体系一直存在着,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发挥着作用,虽然影响力没有那么广泛了。”张文潇看到,供销社也在经历转型。而它真正回归大众视野是在2014年,中央开始在各个省份启动供销社改革试点的工作,重建基层社。
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于本月13日发布。从2004年至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连续20年以“三农”问题为主题,突出了“三农”问题的重要性。而近年来,关于“三农”问题的一大热点话题就是供销社试点改革。
供销社是一个极具年代感的名词,也是一个从未真正离开我们生活的存在,既熟悉又陌生,既遥远又亲近。供销社是什么?它经历过怎样的历史变革?在今天对农村而言又意味着什么?张文潇的栗子故事,或许为我们铺就了一条理解供销社和中国农村的道路。

*(photo:JieMian)01 从栗子看农村如何被城市“抽血”
张文潇:幼年时,我认识到板栗到秋天会成熟,一部分没有来得及采摘的栗子会变成风干栗子,成为当地人家里的零食。有些人家比较富裕,会单独留下一部分板栗,进行储存加工,作为食品。大约上小学后,才渐近接触到“秋天硕果累累”、“农民喜笑颜开”等很多表述,然而,这些与我实际的生活感受存在张力。
在小豆庄的秋天,很难看到神采飞扬、精神奕奕的栗农群体。栗农一般会经历短则十几天、长则一个月的集中性抢收——我在书中描述这是“不舍昼夜”,再夸张一些,就是“舍生忘死”。这是身心的双重折磨,睁开眼就要出门捡栗子,一直到披星戴月地回来。栗农身体经受着考验,大多以透支身体为前提来收获。板栗从树上掉下来滚落四处,栗农得把它们捡起来放进袋子,再蹲、再捡,重复多次,双手布满芒刺,关节也不好受。这还不算扒板栗、扛板栗回家的过程。“过了一个秋像大病了一场一样,”我在当地会听闻这类表述。

*(photo:JieMian)这是生产,还有另外一重风险来自市场,产量多,价格低。板栗流通后,存储难度也会增大,这个压力一部分在栗农身上,但大部分在从事板栗贸易的供销社职工和相关栗贩身上。他们要没日没夜地收购和加工板栗,拉线通宵加工的场景非常常见。
在板栗生产和流通的过程中,供销社的员工会形成聚拢和合作。板栗一天一个价格,他们有一个牌牌,上面写着当日板栗的价格,比如今天板栗四块五,明天可能会变成五块五,后天可能变成六块五。供销社最初是根据果品公司的要求收购相应份额的板栗,然后直接转手。市场打开后,倒购板栗的人拿到板栗以后,往往会集中快速地按照自己心中预定的价格出售板栗。有些胆大的人会把板栗储存起来,甚至会建立库房,以期卖上一个好价格,这样的方式也可能带来数额较大的盈利和亏损。
总而言之,对于栗农和供销社的职工来说,板栗收获就像一场比赛,参赛者肢体困乏,神经紧绷,不知道会获得什么样的嘉奖,但仍然全情投入。
《栗子的故事》
张文潇:这是我的导师赵旭东教授和相关学者的观点。我在书中之所以重述这个观点,是因为它在我的调查中得到了验证。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处于特殊的历史阶段,国家出于全局的考虑,强调工业的建设和发展。以小豆庄为例,小豆庄供销社在收取当地农民的板栗的时候,价格比较低,通过供销社、外贸公司出口到日本时,价格可能翻了两番甚至三四番。这部分盈利是包括供销社在内的流通链条获利的,较少投入到乡村生产和建设中。其他的农业资源在当时也面临着类似的境遇。农民和农村获得的物质补偿在盈利中只占很小的份额。
除了“销”,还有“供”,乡民需要基本的物质生活和生产资料。我在和供销社的老主任进行访谈时发现,相对于城市地区设立的国营公司,供销社卖给乡民的工业品在品次上存在一定的差别。虽然在80年代大力发展乡镇企业,但是生产和制造的工厂仍集中在城市地区,盈利也多流向城市。所以这是城市的抽血过程。这个观点是社会科学家经过多年研究提出来的,是来自于学者的自觉。当然,学界也有不少人持有不同的观点。
张文潇:我在调研中感受到,在集体化经济时期,农民非常认真地投入到国家和集体的建设之中。这并不是说农民没有私欲和私念,比如他们会悄悄在墙边种倭瓜、种小菜,但是他们的观念要么聚焦在自己的家庭,要么关心集体,这类集体是大队乃至国家。但当时因为户籍限制,城乡之间相对分隔,农民群体真正生成城乡之别的认识是比较难的。
随着改革开放逐步演进,农民活动的空间更为广阔,才更多地认识到自己的利益得失,也逐渐看到了城乡差距。贾平凹所著的《极花》给我印象深刻,主人公是一位乡村的男青年,其中一个场景是他忿忿地说:“现在国家发展城市哩,城市就成了个血盆大口,吸农村的钱,吸农村的物,把农村的姑娘全吸走了!”虽然这本书也存在争议,但这在某种程度上反应了农民的一重意识。我也在田野中发现了类似的表达。我听到农民说,农村留不住人;农村什么都不方便,城市里干干净净;人都去建设城市了,把我们都榨干了。

*(photo:JieMian)当然,“抽血”这个比喻在当下乡土社会的事实中正逐渐弱化,国家的倡导和支持大量的资本和资源投入乡村,自上而下地平衡城乡的差距。
02 供销社大势已去但并非一蹴而就
张文潇:欺骗,确实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集体利益的损失,但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也是人们发挥主体性、不断与对其形成压制的强力结构进行博弈的方式。之前,农民、商贩、职员能够获得的利润的份额非常有限。随着个体意识觉醒,才有了这一套行为。这不仅折射了人心的变化,也反映出当时以供销社为代表的集体企业的设计已经跟不上时代的步伐了。
张文潇:供销社大势已去有其时代背景,就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快速转轨。原本非常确定性的计划在遭遇了不确定性的市场时,产生了紊乱和风险。小豆庄的案例就是突出的代表。
“层层欠钱”不过是一种表象,背后是供销社没有办法按照计划经济时期实现对农产品供销情况的全面把控。供销社的盈利一方面来源于收农产品,一方面源于出售工业品。“层层欠钱”不仅涉及以板栗为代表的农产品流通领域,也包括了工业品流通。之前,工业品的流通也是配额制的,工业品非常紧俏,供销社基本不会担负亏损。后来,随着市场体系放开,工业品甚至变得供大于求,供销社出售工业品时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
我在书中写过,供销社进购的布匹太多,卖不出去,只能以很低的价格出售。一位个体经营者得到了这个消息,快速买入,又把它们高价卖到了一个偏远的村庄,赚了很多钱。然而,供销社却不具备此种灵活性。这显示出人们销售和消费的自由度增加了,供销社却没有对此进行及时的反应和调整。这是供销社大势已去的根本原因。

*(photo:JieMian)张文潇:80年代时供销社“还是红火了好几年”,小豆庄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轨不是一蹴而就的。很多人认为1983年尤其是分田到户以后,我们就开始脱离计划经济了,其实不是这样。小豆庄在农产品流通的领域计划经济延续了很久,供销社还是有收购农产品的垄断权,地位还是比较稳固。直到90年代初,人们才有了自主销售收购的权限。
80年代尤其是90年代以后,供销社首先已经不再是基层商品流通的垄断性单位了,开始面临多元的经营主体。当地有集市,有固定经营的个体从业者,还有游街串巷的小贩。农民可以货比三家,和供销社的关系没有那么紧密了。供销社的老主任就曾经批评自己的员工,“再用‘老太爷’的心态去对待农民,那就把你们全部都发配到大集上摆摊卖东西。”
其次,供销社内部的管理也发生了变化。之前员工工资固定,80年代引入市场经济之后,供销社就有了类似于绩效的概念,到了后期自负盈亏。谈到地位变化,还是以小豆庄亏损案为分割点。尽管如此,也并非是突然的边缘化,而是一种渐近的转型。从80年代到90年代出现板栗案的这一时期,供销社主体性地位在渐渐弱化,到90年代亏损五百万之后,供销社没有办法靠自身力量运转,于是把各个门市部分开,每个门市部承包给原有的员工。大家在原址上经营着原来的业务,只是门市部和供销社的关系发生了变化,门市部的负责人不再享受原来的企业福利,开始自负盈亏,也很少承担集体责任,只是每年给供销社租金等成本。这样一直持续到2004年。到2004年以后,小豆庄供销社就不存在了,因为它破产了。但哪怕是在1996年出事后到2004年,原有的门市部在当地还是发挥着重要的商品流通的作用,构成了主要的商业主体。

*(photo:JieMian)03 如何理解今天的供销社?
张文潇:我描述的是一个个案,这可能会造成误会。一些读者也会问,是不是供销社已经不复存在了?相对来说,小豆庄的供销社式微,但是供销社体系一直存在着,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发挥着作用,虽然影响力没有那么广泛了。
供销社真正回归大众视野是在2014年前后,中央开始在各个省份启动了供销社改革试点的工作,比如在广东、山东以及湖北等地有很多供销体系的改革措施。尤其是在湖北,做了一些供销体系的构建,重建了一千多个基层社,引发各界关注。
现在的供销社是在既有供销社的基础之上重建的,是供销社的又一次转型。供销社建立到现在至少经历了两次转型,第一次转型的背景是,计划经济时期供销社充当了以农辅工的中介,而在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就已经开始尝试转而用供销社促进乡村商业的复兴。尤其是在90年代,当时江泽民同志还提到要利用供销社盘活农村的商业和经济。
第二次转型是伴随着“三农”问题的提出而发生的,供销社并不是单纯地发挥经济领域的作用,还在社会结构和组织方面发挥作用,发挥一些服务型的功能,构成了乡村地区重建的组织基础,比如说开始承担社区文化站的工作、承接党员的先锋模范示范点、做组织建设。
现在有一部分供销社在做农村电商下乡的承接单位,沟通着商流和信息流——商流是传统意义上的商品、商业服务、旅游等;信息流就是把城市的信息传送到乡村,把乡村的信息输送到城市,体量比原来单纯的商品流要大得多,信息发布在线上进行。这也是平衡城乡结构的一种尝试,还没有完全实现。
从转型的意义上来看,目前的供销社既不是以农辅工的中介,也不仅仅是促进农村商业复兴的着力点,而是新时代对“三农”问题做出回应的组织基础。也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它尝试构建良性的城乡关系,如今重建仍处于探索阶段,具体能达到什么程度有待静观。

*(photo:JieMian)张文潇:这涉及到供销社的性质问题,供销社到底是国家机构还是集体企业?供销合作总社是由国家相关部门指导的,但是供销社从建立之初到现在都是一个供销合作组织,是激发农民自下而上形成的组织架构。国家是自上而下地发出号召,但真正的资本是从农民这里得到的。你家出二篓棒子、我家出二篓的面,把这些集中在一起,以物易物,换到一些乡民需要的东西摆着卖,盈利再给大家分红。国家最初设计供销社的时候,就是想要打造合作类的组织,并没有想做成国家部门或者机构机关。
农村电商的资本意味很浓厚。在我做田野的地区,供销社还没有完全展开电商,但其他地方已经有一些电商在承接传统供销社的一些业务。但用供销社去做电商,和用某类资本主导建设的平台去做电商是有很大区别的,它不完全是按照市场逻辑运作的,而有一套监管体系,性质上还是以集体利益为导向的。
所以,这里还有一个词是合作力量。如果要实现供销社+电商的理想化发展,就必须强调农民的主体性和合作性。
张文潇:会有这样的困境。我也会担忧,在自由的市场经济中,大家已经非常熟悉自主选择了,这意味着更多的选择空间和自主性。而我们对供销社既有的印象是,从产品价格、数量、定位等都受到严格的管控,计划性远远大于灵活性。
但如果供销社发生一些转型呢?如果供销社会根据需求设计产品、供应产品、对接信息,那可能也会是很好的中介。供销社更需要回应的是生产出来的东西到哪里去卖的问题。
目前,不仅是小豆庄,而且是全国范围的农产品流通出现了非常大的问题。尽管已经进入信息化时代,但市场信息的沟通仍是不充分的,尤其生产农产品时缺乏整体、宏观的调控。今天说山楂赚钱,就全都去种山楂,山楂就可能滞销。如果供销社作为全国的合作性组织,成为及时、快速且相对准确的信息收集机构的话,就可以把相关数据进行集中反馈。这样有助于国家进行整体调控,帮助乡民意识到在哪些方面需要作出调整,这些新建的架构可能会比一些单打独斗的企业更加全面和有效。所以,重建供销社的问题更多地是从全局出发进行思考,通过一个个小机构去盘活一盘棋。
记者 | 潘文捷编辑 | 黄月
1996年,谁也没有想到,有着“政府背景”、垄断了当地商品流通业务近40年的河北省小豆庄供销社(注:小豆庄为匿名),因为板栗业务的失败,导致多个基层供销社和数百位栗农蒙受了高达500万元的损失。这件事成为了当地供销社大势已去的一个标志。
北京城市学院副教授张文潇就来自小豆庄,从一颗小小的栗子入手,她试图厘清包括供销社在内的中国农产品流通体系转型。她在《栗子的故事》一书中写道:“500万亏损案发生后,供销社通过各种方式残喘了八年,长时间的内耗,加之难以与诸多市场主体竞争,供销社在当地的权威形象逐渐被打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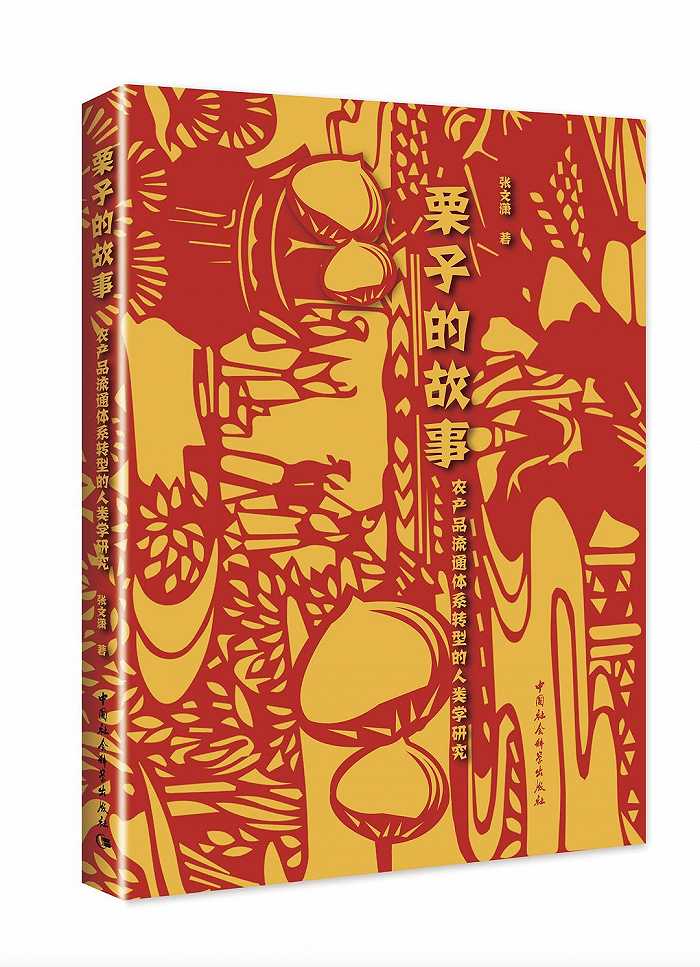
*(photo:JieMian)在张文潇笔下,供销社是这样一个组织,它是不隶属于国家机构的自主联合体,但其功能包括为国有贸易公司收购土产以及销售外来品。在此基础上,两者共同致力于农村贸易的社会主义化。
供销社在不同时期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在社会主义改造期间,从“供”的角度看,供销社管控了农村的消费领域,几乎杜绝了自由买卖的可能;从“销”的角度看,通过对重要农产品和其他物资的计划收购和统一收购,供销社帮助国家实现物资的流通。张文潇看到,这一时期,供销社主要发挥了从乡村汲取资源的作用,助力“以农辅工”。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基层供销社体系面临着诸多挑战,全国各地的许多供销社经历了日渐式微的过程,“但是供销社体系一直存在着,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发挥着作用,虽然影响力没有那么广泛了。”张文潇看到,供销社也在经历转型。而它真正回归大众视野是在2014年,中央开始在各个省份启动供销社改革试点的工作,重建基层社。
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于本月13日发布。从2004年至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连续20年以“三农”问题为主题,突出了“三农”问题的重要性。而近年来,关于“三农”问题的一大热点话题就是供销社试点改革。
供销社是一个极具年代感的名词,也是一个从未真正离开我们生活的存在,既熟悉又陌生,既遥远又亲近。供销社是什么?它经历过怎样的历史变革?在今天对农村而言又意味着什么?张文潇的栗子故事,或许为我们铺就了一条理解供销社和中国农村的道路。

*(photo:JieMian)01 从栗子看农村如何被城市“抽血”
张文潇:幼年时,我认识到板栗到秋天会成熟,一部分没有来得及采摘的栗子会变成风干栗子,成为当地人家里的零食。有些人家比较富裕,会单独留下一部分板栗,进行储存加工,作为食品。大约上小学后,才渐近接触到“秋天硕果累累”、“农民喜笑颜开”等很多表述,然而,这些与我实际的生活感受存在张力。
在小豆庄的秋天,很难看到神采飞扬、精神奕奕的栗农群体。栗农一般会经历短则十几天、长则一个月的集中性抢收——我在书中描述这是“不舍昼夜”,再夸张一些,就是“舍生忘死”。这是身心的双重折磨,睁开眼就要出门捡栗子,一直到披星戴月地回来。栗农身体经受着考验,大多以透支身体为前提来收获。板栗从树上掉下来滚落四处,栗农得把它们捡起来放进袋子,再蹲、再捡,重复多次,双手布满芒刺,关节也不好受。这还不算扒板栗、扛板栗回家的过程。“过了一个秋像大病了一场一样,”我在当地会听闻这类表述。

*(photo:JieMian)这是生产,还有另外一重风险来自市场,产量多,价格低。板栗流通后,存储难度也会增大,这个压力一部分在栗农身上,但大部分在从事板栗贸易的供销社职工和相关栗贩身上。他们要没日没夜地收购和加工板栗,拉线通宵加工的场景非常常见。
在板栗生产和流通的过程中,供销社的员工会形成聚拢和合作。板栗一天一个价格,他们有一个牌牌,上面写着当日板栗的价格,比如今天板栗四块五,明天可能会变成五块五,后天可能变成六块五。供销社最初是根据果品公司的要求收购相应份额的板栗,然后直接转手。市场打开后,倒购板栗的人拿到板栗以后,往往会集中快速地按照自己心中预定的价格出售板栗。有些胆大的人会把板栗储存起来,甚至会建立库房,以期卖上一个好价格,这样的方式也可能带来数额较大的盈利和亏损。
总而言之,对于栗农和供销社的职工来说,板栗收获就像一场比赛,参赛者肢体困乏,神经紧绷,不知道会获得什么样的嘉奖,但仍然全情投入。
《栗子的故事》
张文潇:这是我的导师赵旭东教授和相关学者的观点。我在书中之所以重述这个观点,是因为它在我的调查中得到了验证。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处于特殊的历史阶段,国家出于全局的考虑,强调工业的建设和发展。以小豆庄为例,小豆庄供销社在收取当地农民的板栗的时候,价格比较低,通过供销社、外贸公司出口到日本时,价格可能翻了两番甚至三四番。这部分盈利是包括供销社在内的流通链条获利的,较少投入到乡村生产和建设中。其他的农业资源在当时也面临着类似的境遇。农民和农村获得的物质补偿在盈利中只占很小的份额。
除了“销”,还有“供”,乡民需要基本的物质生活和生产资料。我在和供销社的老主任进行访谈时发现,相对于城市地区设立的国营公司,供销社卖给乡民的工业品在品次上存在一定的差别。虽然在80年代大力发展乡镇企业,但是生产和制造的工厂仍集中在城市地区,盈利也多流向城市。所以这是城市的抽血过程。这个观点是社会科学家经过多年研究提出来的,是来自于学者的自觉。当然,学界也有不少人持有不同的观点。
张文潇:我在调研中感受到,在集体化经济时期,农民非常认真地投入到国家和集体的建设之中。这并不是说农民没有私欲和私念,比如他们会悄悄在墙边种倭瓜、种小菜,但是他们的观念要么聚焦在自己的家庭,要么关心集体,这类集体是大队乃至国家。但当时因为户籍限制,城乡之间相对分隔,农民群体真正生成城乡之别的认识是比较难的。
随着改革开放逐步演进,农民活动的空间更为广阔,才更多地认识到自己的利益得失,也逐渐看到了城乡差距。贾平凹所著的《极花》给我印象深刻,主人公是一位乡村的男青年,其中一个场景是他忿忿地说:“现在国家发展城市哩,城市就成了个血盆大口,吸农村的钱,吸农村的物,把农村的姑娘全吸走了!”虽然这本书也存在争议,但这在某种程度上反应了农民的一重意识。我也在田野中发现了类似的表达。我听到农民说,农村留不住人;农村什么都不方便,城市里干干净净;人都去建设城市了,把我们都榨干了。

*(photo:JieMian)当然,“抽血”这个比喻在当下乡土社会的事实中正逐渐弱化,国家的倡导和支持大量的资本和资源投入乡村,自上而下地平衡城乡的差距。
02 供销社大势已去但并非一蹴而就
张文潇:欺骗,确实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集体利益的损失,但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也是人们发挥主体性、不断与对其形成压制的强力结构进行博弈的方式。之前,农民、商贩、职员能够获得的利润的份额非常有限。随着个体意识觉醒,才有了这一套行为。这不仅折射了人心的变化,也反映出当时以供销社为代表的集体企业的设计已经跟不上时代的步伐了。
张文潇:供销社大势已去有其时代背景,就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快速转轨。原本非常确定性的计划在遭遇了不确定性的市场时,产生了紊乱和风险。小豆庄的案例就是突出的代表。
“层层欠钱”不过是一种表象,背后是供销社没有办法按照计划经济时期实现对农产品供销情况的全面把控。供销社的盈利一方面来源于收农产品,一方面源于出售工业品。“层层欠钱”不仅涉及以板栗为代表的农产品流通领域,也包括了工业品流通。之前,工业品的流通也是配额制的,工业品非常紧俏,供销社基本不会担负亏损。后来,随着市场体系放开,工业品甚至变得供大于求,供销社出售工业品时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
我在书中写过,供销社进购的布匹太多,卖不出去,只能以很低的价格出售。一位个体经营者得到了这个消息,快速买入,又把它们高价卖到了一个偏远的村庄,赚了很多钱。然而,供销社却不具备此种灵活性。这显示出人们销售和消费的自由度增加了,供销社却没有对此进行及时的反应和调整。这是供销社大势已去的根本原因。

*(photo:JieMian)张文潇:80年代时供销社“还是红火了好几年”,小豆庄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轨不是一蹴而就的。很多人认为1983年尤其是分田到户以后,我们就开始脱离计划经济了,其实不是这样。小豆庄在农产品流通的领域计划经济延续了很久,供销社还是有收购农产品的垄断权,地位还是比较稳固。直到90年代初,人们才有了自主销售收购的权限。
80年代尤其是90年代以后,供销社首先已经不再是基层商品流通的垄断性单位了,开始面临多元的经营主体。当地有集市,有固定经营的个体从业者,还有游街串巷的小贩。农民可以货比三家,和供销社的关系没有那么紧密了。供销社的老主任就曾经批评自己的员工,“再用‘老太爷’的心态去对待农民,那就把你们全部都发配到大集上摆摊卖东西。”
其次,供销社内部的管理也发生了变化。之前员工工资固定,80年代引入市场经济之后,供销社就有了类似于绩效的概念,到了后期自负盈亏。谈到地位变化,还是以小豆庄亏损案为分割点。尽管如此,也并非是突然的边缘化,而是一种渐近的转型。从80年代到90年代出现板栗案的这一时期,供销社主体性地位在渐渐弱化,到90年代亏损五百万之后,供销社没有办法靠自身力量运转,于是把各个门市部分开,每个门市部承包给原有的员工。大家在原址上经营着原来的业务,只是门市部和供销社的关系发生了变化,门市部的负责人不再享受原来的企业福利,开始自负盈亏,也很少承担集体责任,只是每年给供销社租金等成本。这样一直持续到2004年。到2004年以后,小豆庄供销社就不存在了,因为它破产了。但哪怕是在1996年出事后到2004年,原有的门市部在当地还是发挥着重要的商品流通的作用,构成了主要的商业主体。

*(photo:JieMian)03 如何理解今天的供销社?
张文潇:我描述的是一个个案,这可能会造成误会。一些读者也会问,是不是供销社已经不复存在了?相对来说,小豆庄的供销社式微,但是供销社体系一直存在着,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发挥着作用,虽然影响力没有那么广泛了。
供销社真正回归大众视野是在2014年前后,中央开始在各个省份启动了供销社改革试点的工作,比如在广东、山东以及湖北等地有很多供销体系的改革措施。尤其是在湖北,做了一些供销体系的构建,重建了一千多个基层社,引发各界关注。
现在的供销社是在既有供销社的基础之上重建的,是供销社的又一次转型。供销社建立到现在至少经历了两次转型,第一次转型的背景是,计划经济时期供销社充当了以农辅工的中介,而在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就已经开始尝试转而用供销社促进乡村商业的复兴。尤其是在90年代,当时江泽民同志还提到要利用供销社盘活农村的商业和经济。
第二次转型是伴随着“三农”问题的提出而发生的,供销社并不是单纯地发挥经济领域的作用,还在社会结构和组织方面发挥作用,发挥一些服务型的功能,构成了乡村地区重建的组织基础,比如说开始承担社区文化站的工作、承接党员的先锋模范示范点、做组织建设。
现在有一部分供销社在做农村电商下乡的承接单位,沟通着商流和信息流——商流是传统意义上的商品、商业服务、旅游等;信息流就是把城市的信息传送到乡村,把乡村的信息输送到城市,体量比原来单纯的商品流要大得多,信息发布在线上进行。这也是平衡城乡结构的一种尝试,还没有完全实现。
从转型的意义上来看,目前的供销社既不是以农辅工的中介,也不仅仅是促进农村商业复兴的着力点,而是新时代对“三农”问题做出回应的组织基础。也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它尝试构建良性的城乡关系,如今重建仍处于探索阶段,具体能达到什么程度有待静观。

*(photo:JieMian)张文潇:这涉及到供销社的性质问题,供销社到底是国家机构还是集体企业?供销合作总社是由国家相关部门指导的,但是供销社从建立之初到现在都是一个供销合作组织,是激发农民自下而上形成的组织架构。国家是自上而下地发出号召,但真正的资本是从农民这里得到的。你家出二篓棒子、我家出二篓的面,把这些集中在一起,以物易物,换到一些乡民需要的东西摆着卖,盈利再给大家分红。国家最初设计供销社的时候,就是想要打造合作类的组织,并没有想做成国家部门或者机构机关。
农村电商的资本意味很浓厚。在我做田野的地区,供销社还没有完全展开电商,但其他地方已经有一些电商在承接传统供销社的一些业务。但用供销社去做电商,和用某类资本主导建设的平台去做电商是有很大区别的,它不完全是按照市场逻辑运作的,而有一套监管体系,性质上还是以集体利益为导向的。
所以,这里还有一个词是合作力量。如果要实现供销社+电商的理想化发展,就必须强调农民的主体性和合作性。
张文潇:会有这样的困境。我也会担忧,在自由的市场经济中,大家已经非常熟悉自主选择了,这意味着更多的选择空间和自主性。而我们对供销社既有的印象是,从产品价格、数量、定位等都受到严格的管控,计划性远远大于灵活性。
但如果供销社发生一些转型呢?如果供销社会根据需求设计产品、供应产品、对接信息,那可能也会是很好的中介。供销社更需要回应的是生产出来的东西到哪里去卖的问题。
目前,不仅是小豆庄,而且是全国范围的农产品流通出现了非常大的问题。尽管已经进入信息化时代,但市场信息的沟通仍是不充分的,尤其生产农产品时缺乏整体、宏观的调控。今天说山楂赚钱,就全都去种山楂,山楂就可能滞销。如果供销社作为全国的合作性组织,成为及时、快速且相对准确的信息收集机构的话,就可以把相关数据进行集中反馈。这样有助于国家进行整体调控,帮助乡民意识到在哪些方面需要作出调整,这些新建的架构可能会比一些单打独斗的企业更加全面和有效。所以,重建供销社的问题更多地是从全局出发进行思考,通过一个个小机构去盘活一盘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