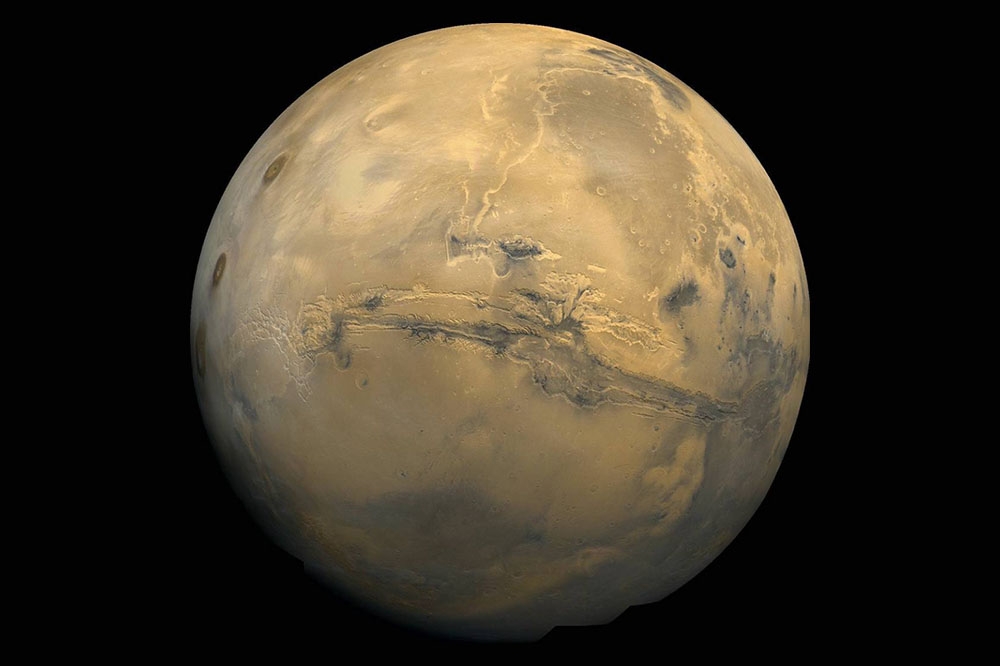对外共享型收租,对内画饼式压榨:从《初创玩家》看WeWork如何乌托邦梦碎
-
记者 | 尹清露编辑 | 黄月
一切都要从房间里的那头独角兽说起。在Apple TV+的新剧《初创玩家(WeCrashed)》的片头曲中,一头高贵的白色独角兽若无其事地穿梭在布满霓虹灯的写字楼和茶水间,直到一曲终了,它的兽角垂直摔落在地,变成一堆碎片。
这大概是对这部剧最好的隐喻,它忠实地描绘了共享办公室企业WeWork从兴起到衰落的全过程。2010年,亚当·诺依曼和他的妻子瑞贝卡·诺依曼在纽约创建了WeWork,旨在为初创公司提供办公场所,不到十年时间,它已经坐拥50多万用户,成为了最炙手可热的“独角兽”公司,甚至得到了软银的巨额投资。如果你去过它在全球任何一间办公楼,可能也会折服于漂亮的装修风格、松软的豆包沙发,以至于产生一种自己也是新时代“数字游民”的美妙幻觉。但事实是,这个估值479亿美元的公司,在短短六周内就濒临破产,创始人亚当也被扫地出门。

*(photo:JieMian)在剧中,主演安妮·海瑟薇和杰瑞德·莱托完美再现了诺依曼夫妇的气质——趾高气扬、自信满满,并深信自己可以改变世界。但就像海报上安妮·海瑟薇那副大到可笑的墨镜一样,夫妇两人的野心有很大的成分是虚张声势,他们不满足于房屋租赁业务,而是自诩为科技公司,号称有1000多名工程师和机器学习专家构建运营系统,但随着时间推移,它最终被证明,所谓的科技成分只是为了撑起估值,其实质上只是个房地产公司。在IPO前夕,商业模式漏洞和财务作假等问题终于暴露出来,WeWork依靠投资公司来实现疯狂扩张的目的昭然若揭。
不仅如此,WeWork的企业愿景也十分夸张,亚当借用了共享经济这一光鲜的概念,提出要建立“资本主义中公社”,一个互相关爱、充满归属感的社区,不断宣扬着要发起一场“我们的革命(We revolution)”,并许诺一个更开放、去中心化的未来。但是WeWork却相继被曝出大肆裁员、超长工作时长,甚至是对员工人格侮辱等新闻。如此种种,这似乎又是另一个“硅谷式骗局”(关于另外的两个骗局,请见这篇文章),但是WeWork的故事仍然值得深思,因为它离我们是如此之近,诸如“未来形态的工作”、“共享社区”的理念即使在国内也拥有大量拥趸。如果亚当的梦想注定要失败,我们能收获的除了另一个硅谷故事,还有什么呢?
01 没有共享的共享经济,没有公平的“公社”
亚当从小生活在一个叫做尼尔安的集体农庄,是以色列乌托邦公社基布兹的其中一个,亚当在那里成长为扎着马尾辫、跳进邻居家泳池裸泳的典型基布兹少年。所以,当亚当来到纽约闯荡时,他被这里的冷漠和疏离震惊了,这种震惊成为了他创业的初衷,进而变成整个品牌故事中最精彩的部分。他一遍遍地面向公众复述这个故事,并让我们相信,我们应该真正地连接彼此,办公室不仅能用来工作,还是一个结交朋友的地方。
故事到这里为止都很温馨,但是亚当接下来的话却暴露出了其矛盾之处,他用怀旧但挑剔的口吻说:“我们需要一个资本主义基布兹,一方面是共享经济,但另一方面,如果你比别人更努力工作,那你也应该得到更多的报酬。” 在基布兹,一个人每天辛苦工作16个小时,而另一个人只需要花一半时间来照顾花园,但两人赚的钱是同样多的,财产都归集体所有,亚当显然觉得这很不合理。

*(photo:JieMian)《澎湃新闻》的《走访以色列基布兹农场:平等主义理想的前世今生》一文指出,基布兹的模式之所以成功,是由于当时的成员难以单独应对生活,他们需要面对阿拉伯人的袭击、资金短缺等问题,而公共生产能提高生产效率,成员们可以以低成本获得各种服务。然而,这些让基布兹得以成立的历史条件在美国并不存在。事实上,由于近几十年来资本主义的渗透,无力偿还银行贷款的基布兹也正经历着巨大危机,在仅存的基布兹社区中,像亚当这样的年轻人的想法其实是非常普遍的。但是如此一来,亚当的做法就无异于抽空了基布兹的平等内核,仅仅留下了它令人感伤的美学层面,在WeWork的入职培训宣传片里,基布兹被美化成一个色调昏黄、与世隔绝的田园,人们穿过大片的薰衣草地,拥抱着彼此。
乍看上去,WeWork确实是个像模像样的社区,因为它的用户大多是千禧一代的科技公司创始人,或者自由职业者,这完美符合了共享经济的去中心化原则,即支持更多的小公司而非大型企业。为了让WeWork的版图扩张至住宅领域,亚当还实行了共同居住实验WeLive,它在功能上是一栋公寓楼,内置了时髦的咖啡馆和餐厅,意义上则是所谓的“实体社交网络”,一群年轻人居住在这里(大多是WeWork的员工),足不出户就可以满足一切日常所需。
虽然这些看上去都很美好,但当我们回想起亚当的话,就会发现事情的一面。在《共享经济没有告诉你的事》一书中,作者汤姆·斯利认为,虽然共享经济通常被看作是商业和非商业活动的多样化集合,但共享经济几乎都是一些得到了风险投资支持的公司,这让它自身成为了社区和企业利益的矛盾混合体。也就是说,WeLive中或许存在着社区成型的某些要素,但那也是为了得到投资人的青睐而下出的一步棋。
研究分享行为的人类学者Thomas Widlok更加直截了当地指出,英语中的“分享”一词经历了非常奇特的发展过程,它已经从分配意义变成了交流意义,在数字平台上分享推文、互相点赞的行为就足以构成“分享”。而WeWork的做法也更偏向后者,它强调的是“在这里你可以遇到知己,甚至是爱人”,但是真正需要分享的空间却得自掏腰包租下。或许,它和共享空间最搭边的举措,就是给每个隔间都装上透明玻璃,让每个人的行为都变得更可见、可计量,可是这反而成为了某种监视,不禁让人想起哲学家韩炳哲口中的“透明社会”而感到战栗。一名WeWork的年轻会计就曾向媒体抱怨过,在报税季节,她必须离开WeWork才能完成工作,因为同事们会不断拍打她的窗户,问她关于现金流或折旧的问题,或者问她能否抽出一个小时来参加康普查品尝小组。
对于亚当来说,能共享的从来只是交流和玩乐的感觉,而不是利益。在《初创玩家》中,当另一个共享空间企业负责人杰米·奥达里来到亚当的办公室,想要商谈合作事宜,亚当却一句话也听不进去,他派人假扮成杰米的样子,坐在标着WeWork logo的快闪车里到对方的公司门口起哄,宣布着要收购对方。讽刺的是,相比起叫嚣着要创立公社的亚当,杰米或许更具有社区精神——“改变世界?不了,我只想做一个有优质服务的公司,并且记住所有员工的名字。”

*(photo:JieMian)02 玩儿命干:零工经济之后的虚假意义感
Wework本来是为企业家服务的,但是很快它就明白,更大的客户群是零工经济下失去庇护的人们。但同样是吸引灵活就业,它和其他共享经济企业的策略之不同在于,零工经济让人们进一步原子化,而WeWork则承诺为自由职业者找到安全感和归属感,提供一个为尊严而改造的工作环境。优步总裁卡兰尼克对建立社区什么的明显并不感兴趣,优步作为平台经济,强调的是经济不稳定的人要自力更生,要有坚韧的美德。而亚当意识到,人们更想听到的其实是安慰,是一句“兄弟,没有人能做到这些,我懂你”。
但是,只有一个温暖的社区是不足以让人为老板卖命的,它还需要让人相信自己的工作值得奔赴。剧中WeWork办公室随处可见的霓虹灯字就是最好的例证,一个写着“做你热爱的事(do what you love)” ,另一个则写着 “玩儿命干(hustle harder)” ,它包含着两层含义:工作必须有足够的价值和意义,而既然它如此有价值,那就应当为此拼命。

*(photo:JieMian)在招聘伊利希亚·肯尼迪(剧中虚构人物)出任首席品牌官时,亚当就是这样说的:“我不是在给你一份工作,而是一份可以触及到几亿人的使命。” 这类画大饼的说辞简直太让人感到熟悉了。按照这个逻辑,值得拼命的工作必须足够有趣和光鲜,重复单调的活计则令人鄙夷,这从人们对那些拥有超级特权的富豪的态度转变就可见一斑——比如,近几年来北美网红卡戴珊家族的名声明显变好了,除了羡慕她们家缠万贯,很多人更赞叹于金·卡戴珊的努力和勤勉,以及她作为女强人和女企业家的身份。
不过就像《卫报》的一篇影评指出的那样,《初创玩家》和《虚构安娜》这类剧集的热播,至少说明我们已经开始反思这种奋斗文化(hustle culture)了。这也是真的,在近期的一则真人秀宣传视频中,金·卡戴珊呼吁人们赶紧起来工作,“最近已经没人认真干活了”。可以想见的是,在疫情肆虐、无数人被迫失业的当下,这番话激起了网友们的猛烈抨击,毕竟不是所有人都拥有她那样优渥的条件。

*(photo:JieMian)像卡戴珊和亚当这样的新一代特权阶级所宣扬的工作伦理之所以受到质疑,是因为他们的话实际上遮蔽了劳资之间根本性的对立关系。在《制造甘愿:垄断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历史变迁》一书中,马克思主义学者迈可·布若威谈到,工业社会学中的许多洞见至今仍然有着解释力,比如工厂是如何利用人们的甘愿心理来进行自我剥削,老板并不会把员工当做自己的下属,而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奖赏体系也全部以个人努力为基准,在这个竞争过程中,员工将工作当做自愿参与的有趣游戏,从而产生一种深层满足感。但是“有趣的工作”也忽略了一个事实,即一群人仍然在出卖劳力换取工资,另一群人则榨取着劳动成果。
亚当的前助理梅根·马洛的经历就是最好的例子,在WeWork梦碎IPO之后,她度过了漫长的心理创伤期,她曾经认为WeWork是她的家,她以成为其中一员而感到骄傲,但她最终得到的是低于其他同类公司的报酬,以及永远无法兑现的优先股权。而亚当即便被赶下台,也可以带着17亿美元的遣散费潇洒离场。
梅根的经历说明了一点,即工作中的意义感有时是多么虚假,尤其是当你无法验证其成果的时候。在当今的美国投资市场上,初创公司先筹集资金再上市的做法,以及投资人害怕错过下一个亚马逊、下一个优步的FOMO心态(fear of missing out),都助长了公司的唯成长论,让他们不得不夸大其颠覆世界的愿景,并变相逼迫员工们为公司的业绩增长努力工作,而当这一切都结束时,剩下的只有深深的被欺骗感。
03 “你是超新星”:WeWork与美国的新时代运动
那么,如果这些意义注定是虚假的,又如何让人长期信服呢?这是WeWork的故事另一个有趣的地方,它涉及到一个重要但往往被忽视了的人物,即亚当的妻子瑞贝卡·诺依曼。
瑞贝卡的头衔是“首席品牌影响官”,然而她并不参与公司的实质运营,有前同事会回忆说,瑞贝卡是那个总在公司里晃来晃去的女人。她也切实地影响到了公司的命运——以一种颇为玄学的方式。在印度达赖喇嘛手下接受过多年的瑜伽训练之后,她把一种新型的“灵修文化”带到了公司,这种文化首先就非常有效地激励着亚当,在剧中,每次亚当要做出什么重大决定,她便以一种十分令人信服地口吻说:“别忘了,你是超新星,你可以做得到。” 在WeWork的夏令营活动里,她要求员工们手拉着手,感受一种来自“我们”的团结能量。

*(photo:JieMian)虽然硅谷创业者和东方禅学的故事已经屡见不鲜,甚至成为某种刻板印象,上述的例子听上去也有点好笑,但是瑞贝卡的做法恰巧是在为WeWork创造着它最需要的意义感。如果把平台经济的雇员绑定在一起的是平台本身——因为他们不得不依靠于此赚钱——那么把WeWork的员工绑定在一起的则是瑞贝卡发明的那句公司宗旨:“提升全人类的意识。”当然,没人知道这句邪教般的口号是什么意思,但是你尽可以把象征美好未来的说辞都塞进去,诸如颠覆世界、成为更大存在的一部分等等,当记者问起一些尖锐的财务问题时,便可以用这些说辞蒙混过关。
瑞贝卡所相信的灵修文化其实根植于美国的新时代运动(New Age Movement),它起源于上世纪60年代的嬉皮士运动并持续到了当代,也由于它的实践变得越来越广泛而几乎难以再称之为是一项运动。人类学者潘天舒指出,新时代运动的首要特征就是摒弃了以教堂为中心的一神教模式,成为了一种“宗教合成主义”,万物有灵论和风水这类古老的词汇反而成为了它标志性的语言符号。它还认为参与者只能聆听内心的声音、听从灵感的召唤,而不是传教士的布道。
这样一来,瑞贝卡那些关于心灵自我说辞就难以攻破,因为它的源头本身就不是单一的教义。同时,新时代运动中的许多理念也可以为她所用,比如反抗教条、对个人主义的注重,以及对于“直接沟通”的痴迷。WeWork的员工们就认为自己可以通过虔诚地相信,从而直接成为社区中的一员。
你可能会哀叹于,这些东海岸嬉皮士的精神遗产被大型商业给收编了,但是,在批判硅谷创业热潮的著作《What Tech Calls Thinking》中,作者Adrian Daub却提醒我们,事实上,反主流文化的大部分都依赖于大企业,比如人们对越南战争和政府的厌恶经常转化为一种信念,即商业才是人类组织更自然、自发的形式,也更不容易被滥用或出现暴政,只不过WeWork的故事再次印证了这一信念的天真和单纯。我们也会猜测,来自基布兹的小男孩亚当是否也曾怀抱过这样的信念,而瑞贝卡那鼓舞人心的魔力如果施展在其他领域,会不会有不一样的结果呢。就像WeWork的前员工说过的那样,即使离开了公司,他们还是会想念彼此之间的友谊,那是不可磨灭的。但是,社区精神毕竟无法在对往日的怀旧、美国梦的追求,以及现代公司制度的混合物中自行生长出来,这可能是整个故事中最令人惋惜的部分。
参考资料:
“The Rise of the WeWorking Class | The New York Times”
https://www.nytimes.com/interactive/2019/02/21/magazine/wework-coworking-office-space.html
“Why WeWork went wrong | WeWork | The Guardian”
https://www.theguardian.com/business/2019/dec/20/why-wework-went-wrong
“Hustle harder: how TV became obsessed with stories of workism | US television | The Guardian”
https://www.theguardian.com/tv-and-radio/2022/mar/31/wecrashed-hustle-harder-tv-workism
Daub, Adrian. (2020) What Tech Calls Thinking: An Inquiry into the Intellectual Bedrock of Silicon Valley, FSG Originals.
Widlok,Thomas. (2017) Anthropology and the Economy of Sharing, Routledge.
走访以色列基布兹农场:平等主义理想的前世今生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405587
《热血野心:优步的崛起与衰落》 [美]迈克·艾萨克 著 潘珣祎 阮佳程 俞晔娇 译 中信出版社 2021-8
《制造甘愿:垄断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历史变迁》 [美] 迈克尔·布若威 著 林宗弘等 译 群学出版社 2005-4
《共享经济没有告诉你的事》 [加] 汤姆·斯利 著 涂颀 译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17-3
《文化全球化与多元信仰实践:美国“新时代运动”的人类学解读》 潘天舒 思想战线 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