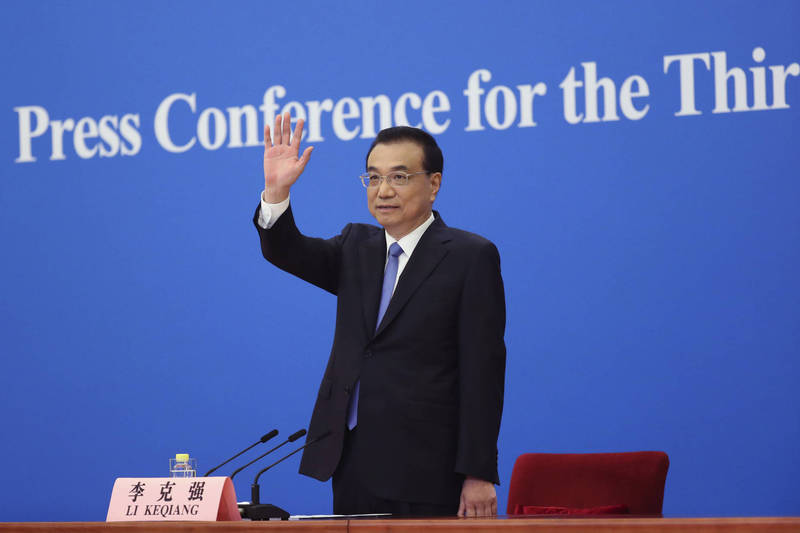中国新修订的妇女权益保障法的具体落实和监督面临挑战
-

北京一名抗议者手持“我也是 #me too”的牌子站在将要审理一桩性骚扰案的法庭外。(2020年12月2日)(photo:VOA)台北 - 11月5日,中国媒体今日头条的帐号曝光了重庆移通学院院长、同时也是作家的丁伯慧,因为长期性骚扰女性下属而落马。这反映了性骚扰或成为很多中国女性的职场困扰之一。另一方面,中国最近新修订了妇女权益保障法,以提倡男女平等和提升妇女的权益。但分析人士说,这项立法精神,固然值得肯定,但跟中国目前强调孝道,将女性角色拉回到家事领域的政治走向似有些矛盾,而且它比较像是一个纲领性的法律,如何具体落实与监督将是一大疑问。
中国人大会议上月底审议通过了中国妇女权益保障法修定草案,这是该法自1992年实施近30年来第二次“大修”,上一次的全面修订是在2005年。新的修订草案内容将男女平等纳入基本国策教育,并回应近年来中国社会关注的性别歧视、防治性侵、性骚扰、家庭暴力、拐卖与绑架等妇女维权热点问题。
修订后的妇女权益保障法草案一共有10章,共86条,自2023年1月1日起实施。
男女平等是基本国策
修订草案指出,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人身和人格权益;妇女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妇女的人格尊严;禁止进行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特殊治疗时,应当征得妇女本人同意;在妇女与其家属或者关系人意见不一致时,应当尊重妇女本人意愿。
法案中也明文指出,禁止拐卖、绑架妇女,也禁止收买与阻碍解救被拐卖、绑架的妇女。同时禁止违背妇女意愿,以言语、文字、图像、肢体行为等方式对其实施性骚扰。受害妇女可以向有关单位和国家机关投诉。接到投诉的有关单位和国家机关应当及时处理,并书面告知处理结果。
美国之音采访了一位在北京从事第一线妇女维权工作的社工师小玉,她今年31岁,因为安全因素使用化名,她对美国之音说,这份修订草案是一部纲领性的法案,虽然里头提到各种妇女应该享有的平等权利,但不够细致,以致对妇女的实质助益有限。
法案跟实际执行有落差
她表示,在她实际介入协助处理各式性骚、性侵或家庭暴力的个案时,常常要跟警方、公安部门打交道,或者当家暴性侵案件进入司法程序后,在诉讼的过程需要向警方或社区人员取得一些相关资料,但对方时常会以“这是他们家私人的事情,我们不适合介入”为由,拒绝提供协助。
小玉表示,也就是说,即使中国有了一部妇女权益保障法,里面也有相关规定,但实际上这些条款没有具体规定到如果这些部门不配合执行的话,会有什么后果与惩罚,“所以它基本上就是一个有点像是宪法一样的精神性纲领法律,只是告诉大家,我们中国有这样一部法律。”
小玉表示,她接触到最多的投诉个案是关于家暴、性骚扰、性侵害,以及职场性别歧视的问题,但不同阶段也有不同的变化。她说,在2018年全球掀起“#Me too 我也是”风潮时,他们接获很多讲述自身遭到性骚经历的个案,占了投诉案件的一半;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后,他们接到更多的是关于家暴方面的案件;现在则是各类投诉都有,有受到亲密伴侣缠扰的,有职场性骚扰的,也有在亲密关系里遭到性侵的。
生完二胎丢了工作
方小姐今年38岁,在南京从事文化工作,目前仍然单身。尽管她本身从来没有遭遇性别歧视的经历,但是她告诉美国之音,中国企业普遍不太喜欢怀孕的女性,更别说是二胎,她有一位好朋友就是受害者。她说,她的朋友在怀第二胎时,主管常常有意无意地透露请假产检会造成其他人的工作负担,给她脸色看。她说,虽然国家有法律保护职场中的孕妇,但实际上当她朋友生产完后再回去上班时,公司用各种方法刁难她,请她离开,最后那位朋友丢掉了那份工作。方小姐认为,修订草案应通过各种激励机制来解决这个实际问题。
分析人士说,中国新修订的妇女保障法涵盖范围广泛,从立法精神来看,值得肯定,但不管在哪个国家,“法”永远都只是一个最低门槛,如何具体落实更重要。

台湾清华大学社会学研究所副教授沈秀华。(沈秀华提供)(photo:VOA)台湾清华大学社会所副教授沈秀华是中国性别研究的专家,她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过去在毛泽东时代喊出“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口号,但事实上很多研究显示,中国妇女在当时社会主义下也没有真的撑起半边天,但她们至少在公共领域还能有一定程度的参与。
“但是经改之后,很多女性权益是往后倒退的,”沈秀华说。
她表示,在中国经改后,国家资产私有化的过程,造成了“国家退、家庭进”的结果,比如社会安全网的建立就退回到以家庭为核心,此时女性就很容易落入到传统家庭角色里,女性公共参与的空间因此逐渐限缩,薪资结构和权力分配也越来越差。男性在经改里的政治与经济地位远远高过女性,二元性别的角色更加被强化,女性被要求回归家庭。
被推回传统家事领域
沈秀华说,虽然修订草案强调男女平等,但实际上在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脉络下,当局不断强调孝道,女性比从前更加被推回到传统的家事领域。中国现在又面临人口老龄化的危机,国家鼓励生育“三孩政策”,虽然妇女权益保障法修订草案有提到不能强迫女性生育,但在国家、社会、家庭、亲友敦促女性多多生育的情况下,无形中造成妇女更大的压力;在双薪家庭的趋势下,女性又不得不出来工作,所以中国女性处境越来越艰难。
此外,她说,当家庭要承担更多个人照顾与生活的责任时,不只是青壮年的中国女性在照顾方面的工作会加重,年老或退休女性的照顾工作也会增加,因为他们要帮忙儿女照顾下一代,还要照顾自己的伴侣。
沈秀华说:“就是说(中国)政治目前的走向是跟它这个法的走向,其实是有矛盾的,它现在政治上推动的一些以家庭为主,要求女性负担起更多家庭照顾各方面的家务,但是同时,女人也要出来工作。可是现在有一个问题是说,到底执政的部分,还有整个执法的部分,我看到那个准则是有要求落实到县级,那地方政府会怎么去落实到各层政府,这个就变成很大的疑问。”
谁来监督执法成效
她表示,另一个问题是,当中国不允许公民社会的存在时,谁来监督执法成效,而监督机制又是什么,“我想这应该是所有人都会有的问号”。
中国妇女权益保障法修订草案指出,妇女有权依法参与管理国家事务,全国和地方人大代表中要保证有适当数量的妇女代表,国家机关等在选拔和任用干部时,应坚持男女平等的原则,让适当数量的妇女担任领导职务。
但是,在上月选出的中共二十大中央政治局委员里,没有一位女性,这打破了过去二十年来的惯例。
在美国的中国女权运动倡导者吕频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过去中共中央政治局里有一位女性也只是一个象征性的意义,没有实质上的作用,因为女性代表必须要达到一定的比例才有可能推动一些妇女权益工作,所以若想指望这一、两名女性代表的存在就能推动妇女工作,是不可能的、也做不到。

中国女权倡导者吕频。(吕频提供)(photo:VOA)她并表示,外界若以为过去政治局里有一位女性代表,就意味着当时的女性地位比现在高,“那也是不真实的”。
妇女权利难有实质性变化
她说:“从这个角度来说,有一个女性和没有女性,它不会给中国的妇女权利带来什么实质性的变化,它带来的变化只有一点,就是说以前政府还比较觉得需要做这样的表演,今天的二十大的时候,政府、党觉得自己不需要做一个表演,我觉得关键是在这儿。”
吕频表示,中国妇女权益保障法自1992年出台至今,没有发挥什么作用,“我们还怎么能够指望这次修订能给妇女权利带来什么实质性的推动?”她说,威权国家的文书往往写得非常冠冕堂皇,“但文宣跟实质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她认为,如果轻信威权国家的文书言词就会有很多失望,中国民众在这一方面已经受过足够训练,不会相信、也知道这样的法条言词没有意义。
吕频说,女权团体十分关心女性参与政治的权利,但这无关乎政治局里有没有一位女性代表,而是在于女性能不能用自己希望的方式,来公开谈论自己关心的议题,这是中国女权运动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因为话语权一但被剥夺,很多权利就无法伸张。
她说,倡导女权的帐号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几乎都全被禁言,而这只是被中共剥夺话语权的众多群体之一。当中共本身的威权加深、与公民团体协商的空间已不存在的时候,若还设想政府立法可以如何促进妇女权益,无疑是与虎谋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