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者许纪霖:“西学原罪论”是一种偷懒的批评方式
-
界面新闻记者 | 林子人界面新闻编辑 | 黄月
在谈到中国以外的学者对有关中国的方方面面进行研究的学科时,我们往往会用汉学(Sinology)或中国学(Chinese Studies)来称呼。汉学始于欧洲,最初是对古代中国的研究。
中国研究则始于20世纪中叶的美国。1939年,美国汉学家、历史学家费正清与历史学家、日本问题专家埃德温·赖肖尔一同在哈佛大学开设了东亚文明课程;1955年,费正清创建了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培养出了一批学者,他们前往全美各个大学推广中国研究,让美国成为当代海外中国研究的重地。
1988年起,江苏人民出版社推出“海外中国研究丛书”,译介海外汉学研究成果,至今已出版图书225种,囊括的作者有费正清、孔飞力、周锡瑞、魏斐德等。

*(photo:JieMian)在这套丛书出版35年之际,澳门大学历史系讲席教授王笛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特聘教授许纪霖以“我们为什么要读海外汉学”为题日前展开讨论。
在许纪霖看来,海外中国研究中的优秀作品给中国学者带来了诸多研究和写作方面的启示。但近年来有一种声音认为海外中国研究价值有限、不值得讨论,推崇本土化的理论,他认为这种“西学原罪论”是一种很偷懒的批评,“甚至称不上是一种学术批评,良性的学术交流应当是对所有研究保持好奇开放的心态。”
西方学者能注意到中国学者想不到的问题
许纪霖谈到,在上世纪80年代还有若干影响了中国文化、学术进程的丛书,但都已不再出版。而能把“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做到35年,“某种意义上是一个‘奇迹’。”
这套丛书中让许纪霖印象最深刻的,是史华慈的《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史华慈“以问题为中心”的思想史研究方法深刻影响了他的治学和其他许多思想史学者。他注意到,《寻求富强》出版后在国内受到了一些批评,认为史华慈没有描述一个“客观、全面的严复”。但在许纪霖看来,这恰恰是史华慈的研究特色,“他把严复复杂思想中的某一个面抽象出来、凸显出来,达到片面的深刻,从而形成他的问题导向。”史华慈在书中指出,严复比同时代的西方思想家更敏锐地注意到,寻求富强是19世纪欧洲思想的核心动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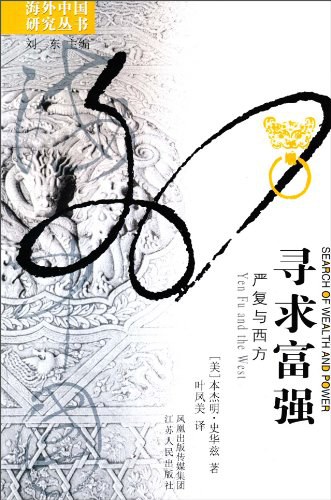
*(photo:JieMian)王笛于1991年到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攻读历史学博士学位,之后每次回国,“海外中国研究丛书”都在他的购书单上。作为研究日常生活的历史学者,丛书中谢和耐的《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给了他很多启发。这本1950年代首次出版的作品,到了1990年代几乎仍然是西方研究中国日常生活的唯一专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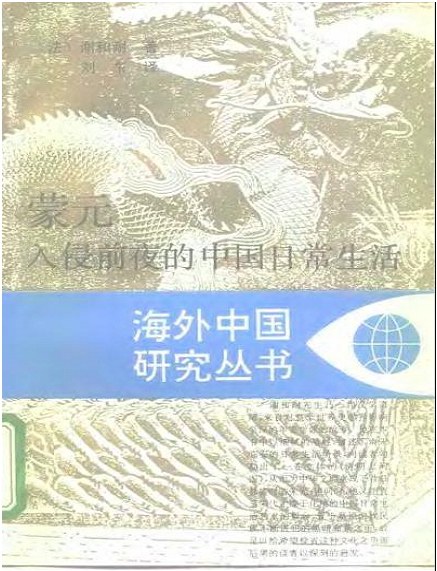
*(photo:JieMian)王笛回忆道,中国学界长期流传一个观点,即“西方学者无论如何都研究不过中国人”,因为中文很难,文言文更难,西方人理解中国无异于“隔靴搔痒”。但在“这套丛书出版后,中国学界才发现西方学者的研究课题、使用的资料和挖掘资料的方式往往能带来一些新的认识。“有时候我们是‘身在庐山’,有些问题不一定能够意识到,而西方汉学家作为他者,看中国的问题甚至是我们没有想到的问题。”
他以高彦颐的《闺塾师》为例,解释了西方历史学者如何为中国史研究带来新的视角。这本书挑战了“中国妇女在历史上是受压迫的”这一传统历史叙事,提醒读者注意古代中国妇女生命经验的复杂性。高彦颐在研究明末江南士绅家庭女性的过程中发现,她们能够接受很好的教育。王笛认为,这一发现给我们展示了中国传统社会妇女的另外一面,提醒我们历史中经常会出现“例外现象”,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也影响了他自己的研究。王笛在研究晚清四川社会改良时发现,我们不能想当然地认为社会改良者肯定对妇女采取更为开放包容的态度,事实是,恰恰是这些改良派对妇女参与公共生活提出了更多的限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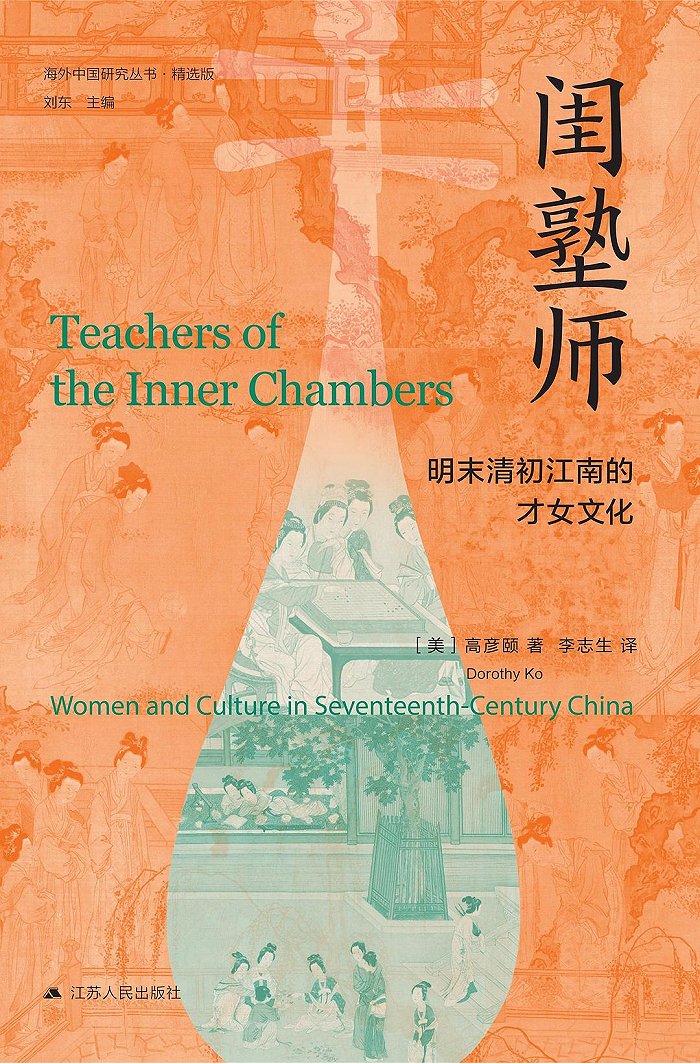
*(photo:JieMian)美国的中国研究强在体系开放
许纪霖指出,美国的中国学在1980年代出现了重要转向。80年代以前的美国学者大多专注于政治史、外交史和思想史研究,80年代以后,大量海外学者可以来中国查阅资料,同时又受到了法国年鉴学派的影响,社会史、文化史、生态史、性别史也开始进入史学视野。
另外一个转向是学界对历史的理解出现了重大变化。“过去我们总是相信历史有真相,这个真相是唯一的。现在很多中国的历史学家依然相信历史有客观真相,历史学家的唯一目标就是通过发掘史料,揭示这个真相。上世纪80年代以后,历史本质主义被破除,对历史了解越深入越会发现:在这个复杂的世界,已经发生的历史对后人来说是开放的,可以作多元的解读,不同的史料可以整合成不同的真相、不同的图景。”
许纪霖指出,美国后本质主义哲学推进了史学的发展,比如新文化史的出现——这一细分领域受福柯后现代理论的影响,认为现实很大程度上是文化建构的产物。柯文的《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就运用了新文化史的理论方法。
“美国的中国研究学者借鉴欧洲,对日本也有借鉴。此外,他们可以把其他学科的好东西吸纳进来。但是不要以为中国学者在这部分是缺席的。中国的学者,包括晚清民国时期和一些中国当代学者也都非常擅长倾听、理解、接纳。美国的中国研究之所以这么强,因为它是一个开放的体系。”他说。
“西学原罪论”是一种偷懒的批评方式
许纪霖从问题意识和叙事方式两个角度阐述了海外中国研究的重要价值。首先,国外一些学者也许在史料挖掘方面未必有新意,但他们有突出的问题意识。他注意到,中国学生在研究时往往遵循“以论代史”的传统研究模式,先看资料,论从史出。这样的研究方法固然也能做出好的研究,但也有很多资料虽扎实、结论没有任何新意的平庸之作。
与此同时,海外中国研究中的优秀作品能够提出非常重要的概念。杜赞奇在《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中探究的核心问题是:中国政府的权力如何渗透到基层乡村?在这本体量不大的书中,他提出了“权力的文化网络”这个概念,揭示了政府权力无法脱离血缘、地缘、信缘等既有文化网络运作。许纪霖认为,杜赞奇为学界提供了一个具有相当解释力和某种普遍意义的分析性概念。他指出,中国本土学者也曾具有这种超越一时一地的研究、提炼出分析性概念的能力,比如费孝通的“以自我为中心的差序格局”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
许纪霖注意到,近年来无论是大众读者还是学界内部都渐渐出现了一种声音,认为海外中国研究的价值有限,提倡本土化的理论,他把这种认为西方观点不值得讨论的声音概括为“西学原罪论”。他认为这是一种很偷懒的批评,甚至称不上是一种学术批评。因为学术研究不是奥林匹克竞赛,存在“孰优孰劣”,良性的学术交流应当是对所有研究保持好奇开放的心态,什么都读但绝不迷信,“吃百家饭,采百家花,最后酿成自己的蜂蜜。”
王笛认为,当下我们对历史学的理解建立在西方现代历史学的基础之上,因此我们无法回避西方的理论与方法,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需要对海外中国研究,哪怕是汉学经典顶礼膜拜,而是应该用批判的态度去广泛阅读。“当西方学者在研究美国史、欧洲史的时候,或者日本学者在研究日本史的时候,也引用我们中国学者对中国史的研究——到了那个程度,可以说我们的历史研究是真的走向了世界。”
界面新闻记者 | 林子人界面新闻编辑 | 黄月
在谈到中国以外的学者对有关中国的方方面面进行研究的学科时,我们往往会用汉学(Sinology)或中国学(Chinese Studies)来称呼。汉学始于欧洲,最初是对古代中国的研究。
中国研究则始于20世纪中叶的美国。1939年,美国汉学家、历史学家费正清与历史学家、日本问题专家埃德温·赖肖尔一同在哈佛大学开设了东亚文明课程;1955年,费正清创建了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培养出了一批学者,他们前往全美各个大学推广中国研究,让美国成为当代海外中国研究的重地。
1988年起,江苏人民出版社推出“海外中国研究丛书”,译介海外汉学研究成果,至今已出版图书225种,囊括的作者有费正清、孔飞力、周锡瑞、魏斐德等。

*(photo:JieMian)在这套丛书出版35年之际,澳门大学历史系讲席教授王笛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特聘教授许纪霖以“我们为什么要读海外汉学”为题日前展开讨论。
在许纪霖看来,海外中国研究中的优秀作品给中国学者带来了诸多研究和写作方面的启示。但近年来有一种声音认为海外中国研究价值有限、不值得讨论,推崇本土化的理论,他认为这种“西学原罪论”是一种很偷懒的批评,“甚至称不上是一种学术批评,良性的学术交流应当是对所有研究保持好奇开放的心态。”
西方学者能注意到中国学者想不到的问题
许纪霖谈到,在上世纪80年代还有若干影响了中国文化、学术进程的丛书,但都已不再出版。而能把“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做到35年,“某种意义上是一个‘奇迹’。”
这套丛书中让许纪霖印象最深刻的,是史华慈的《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史华慈“以问题为中心”的思想史研究方法深刻影响了他的治学和其他许多思想史学者。他注意到,《寻求富强》出版后在国内受到了一些批评,认为史华慈没有描述一个“客观、全面的严复”。但在许纪霖看来,这恰恰是史华慈的研究特色,“他把严复复杂思想中的某一个面抽象出来、凸显出来,达到片面的深刻,从而形成他的问题导向。”史华慈在书中指出,严复比同时代的西方思想家更敏锐地注意到,寻求富强是19世纪欧洲思想的核心动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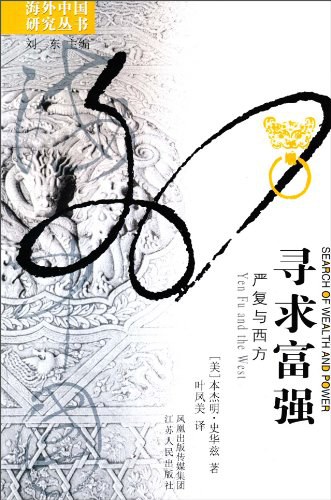
*(photo:JieMian)王笛于1991年到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攻读历史学博士学位,之后每次回国,“海外中国研究丛书”都在他的购书单上。作为研究日常生活的历史学者,丛书中谢和耐的《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给了他很多启发。这本1950年代首次出版的作品,到了1990年代几乎仍然是西方研究中国日常生活的唯一专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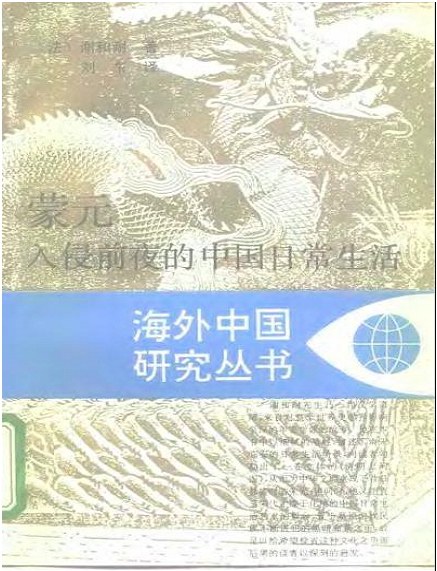
*(photo:JieMian)王笛回忆道,中国学界长期流传一个观点,即“西方学者无论如何都研究不过中国人”,因为中文很难,文言文更难,西方人理解中国无异于“隔靴搔痒”。但在“这套丛书出版后,中国学界才发现西方学者的研究课题、使用的资料和挖掘资料的方式往往能带来一些新的认识。“有时候我们是‘身在庐山’,有些问题不一定能够意识到,而西方汉学家作为他者,看中国的问题甚至是我们没有想到的问题。”
他以高彦颐的《闺塾师》为例,解释了西方历史学者如何为中国史研究带来新的视角。这本书挑战了“中国妇女在历史上是受压迫的”这一传统历史叙事,提醒读者注意古代中国妇女生命经验的复杂性。高彦颐在研究明末江南士绅家庭女性的过程中发现,她们能够接受很好的教育。王笛认为,这一发现给我们展示了中国传统社会妇女的另外一面,提醒我们历史中经常会出现“例外现象”,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也影响了他自己的研究。王笛在研究晚清四川社会改良时发现,我们不能想当然地认为社会改良者肯定对妇女采取更为开放包容的态度,事实是,恰恰是这些改良派对妇女参与公共生活提出了更多的限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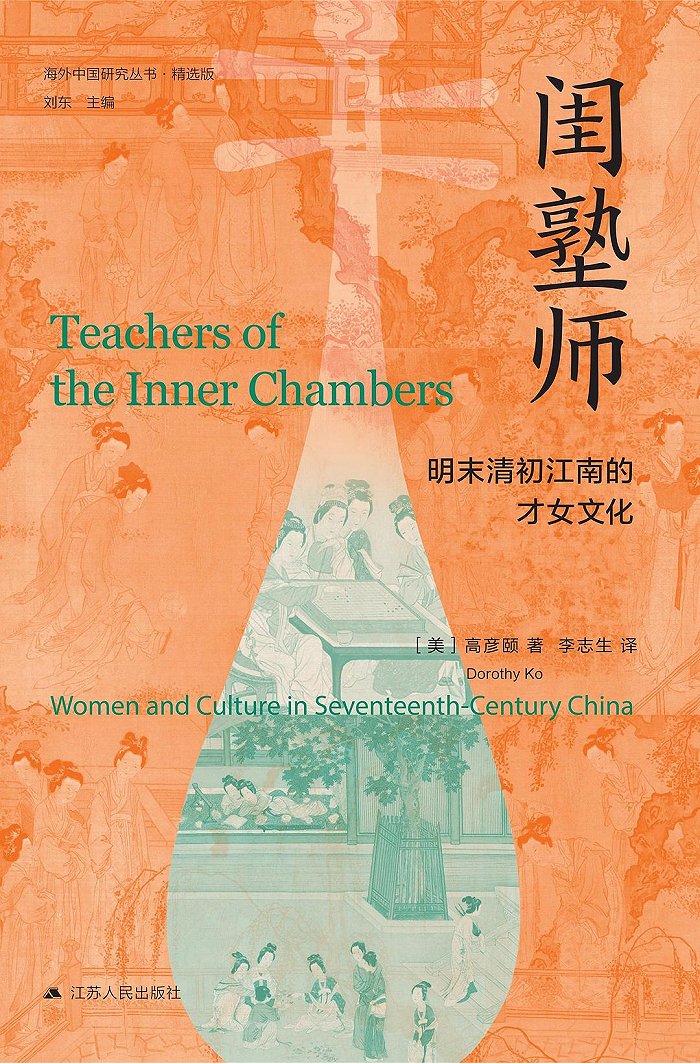
*(photo:JieMian)美国的中国研究强在体系开放
许纪霖指出,美国的中国学在1980年代出现了重要转向。80年代以前的美国学者大多专注于政治史、外交史和思想史研究,80年代以后,大量海外学者可以来中国查阅资料,同时又受到了法国年鉴学派的影响,社会史、文化史、生态史、性别史也开始进入史学视野。
另外一个转向是学界对历史的理解出现了重大变化。“过去我们总是相信历史有真相,这个真相是唯一的。现在很多中国的历史学家依然相信历史有客观真相,历史学家的唯一目标就是通过发掘史料,揭示这个真相。上世纪80年代以后,历史本质主义被破除,对历史了解越深入越会发现:在这个复杂的世界,已经发生的历史对后人来说是开放的,可以作多元的解读,不同的史料可以整合成不同的真相、不同的图景。”
许纪霖指出,美国后本质主义哲学推进了史学的发展,比如新文化史的出现——这一细分领域受福柯后现代理论的影响,认为现实很大程度上是文化建构的产物。柯文的《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就运用了新文化史的理论方法。
“美国的中国研究学者借鉴欧洲,对日本也有借鉴。此外,他们可以把其他学科的好东西吸纳进来。但是不要以为中国学者在这部分是缺席的。中国的学者,包括晚清民国时期和一些中国当代学者也都非常擅长倾听、理解、接纳。美国的中国研究之所以这么强,因为它是一个开放的体系。”他说。
“西学原罪论”是一种偷懒的批评方式
许纪霖从问题意识和叙事方式两个角度阐述了海外中国研究的重要价值。首先,国外一些学者也许在史料挖掘方面未必有新意,但他们有突出的问题意识。他注意到,中国学生在研究时往往遵循“以论代史”的传统研究模式,先看资料,论从史出。这样的研究方法固然也能做出好的研究,但也有很多资料虽扎实、结论没有任何新意的平庸之作。
与此同时,海外中国研究中的优秀作品能够提出非常重要的概念。杜赞奇在《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中探究的核心问题是:中国政府的权力如何渗透到基层乡村?在这本体量不大的书中,他提出了“权力的文化网络”这个概念,揭示了政府权力无法脱离血缘、地缘、信缘等既有文化网络运作。许纪霖认为,杜赞奇为学界提供了一个具有相当解释力和某种普遍意义的分析性概念。他指出,中国本土学者也曾具有这种超越一时一地的研究、提炼出分析性概念的能力,比如费孝通的“以自我为中心的差序格局”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
许纪霖注意到,近年来无论是大众读者还是学界内部都渐渐出现了一种声音,认为海外中国研究的价值有限,提倡本土化的理论,他把这种认为西方观点不值得讨论的声音概括为“西学原罪论”。他认为这是一种很偷懒的批评,甚至称不上是一种学术批评。因为学术研究不是奥林匹克竞赛,存在“孰优孰劣”,良性的学术交流应当是对所有研究保持好奇开放的心态,什么都读但绝不迷信,“吃百家饭,采百家花,最后酿成自己的蜂蜜。”
王笛认为,当下我们对历史学的理解建立在西方现代历史学的基础之上,因此我们无法回避西方的理论与方法,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需要对海外中国研究,哪怕是汉学经典顶礼膜拜,而是应该用批判的态度去广泛阅读。“当西方学者在研究美国史、欧洲史的时候,或者日本学者在研究日本史的时候,也引用我们中国学者对中国史的研究——到了那个程度,可以说我们的历史研究是真的走向了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