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里的冬日童年:克瑙斯高的烟花与乌格雷西奇的煤灰
-

图片来源:Clark Wilson Unsplash图片来源:Clark Wilson Unsplash(photo:JieMian)编者按:
童年时代,冬天的关键词有哪些?烟花?白雪?家庭生活?在挪威作家卡尔·奥韦·克瑙斯高的《在冬天》里,在克罗地亚裔荷兰作家杜布拉夫卡·乌格雷西奇的《无条件投降博物馆》里,两位作家写下了自己印象中的冬天。
同样是回忆童年的冬天,同样围绕着父母与家庭生活展开,他们呈现出了不同的情感:克瑙斯高“炫耀”起自家放烟火的技术,认为这正是比起邻居更高明的地方;乌格雷西奇描述煤灰落在积雪上的场景,孩子们先抹去雪上的黑灰,再将小小的身体印在白雪上。
有趣的是,他们也都透露了童年居住的环境。彼此差不多、生活集体共享是这两位作者的共同记忆点。克瑙斯高的小区由一长排相同的房子组成,乌格雷西奇的家则在工人新村,母亲会带着她去公共澡堂洗澡。那些关于烟花与煤灰的记忆,或许也与中国读者记忆中的童年相通。
克瑙斯高:烟花
我喜欢烟花,但不是那种限于地面或浮于地面的烟花,例如爆竹、圣诞拉炮、烟火棒、地面旋转式烟花、喷泉礼花这些,我对烟花的钟爱仅限于那种带引信点火装置的烟花,它能在高高的夜空中展现它的辉煌。从我记事起,我就一直喜欢这种烟花。小时候我在一个住宅区长大,也就是一长排相同房子的中间,里面有一样的车道,周围都是大小相同的花园,虽然每家每户发生的事情各不相同,但表面来看大家的生活都差不多。
最大的例外是新年夜,在午夜前后的几小时内,特别是在十二点前的最后几分钟和之后的几分钟里,所有孩子都会站在他们的母亲身旁,到花园里看父亲弯腰给爆竹的保险丝点火,直到保险丝着了火,父亲才会跑回来和其他人一起,站着看爆竹离开地面,升到空中,带着噼啪作响的花火飞到高空,不仅这一家子人能看到,甚至后墙外的人,以及所有其他住宅区的居民都能看到。烟花就这么每年一次地照亮了每个人心中真正的想法,也照出了每个人的真实身份。哎呀!这五彩缤纷的颜色,这绚丽夺目的光辉,不仅爆炸式地喷涌而出,还会悬在天上,再慢慢坠落,洒在漆黑的夜空中,告诉所有人它们的出处。至少在我父亲看来是这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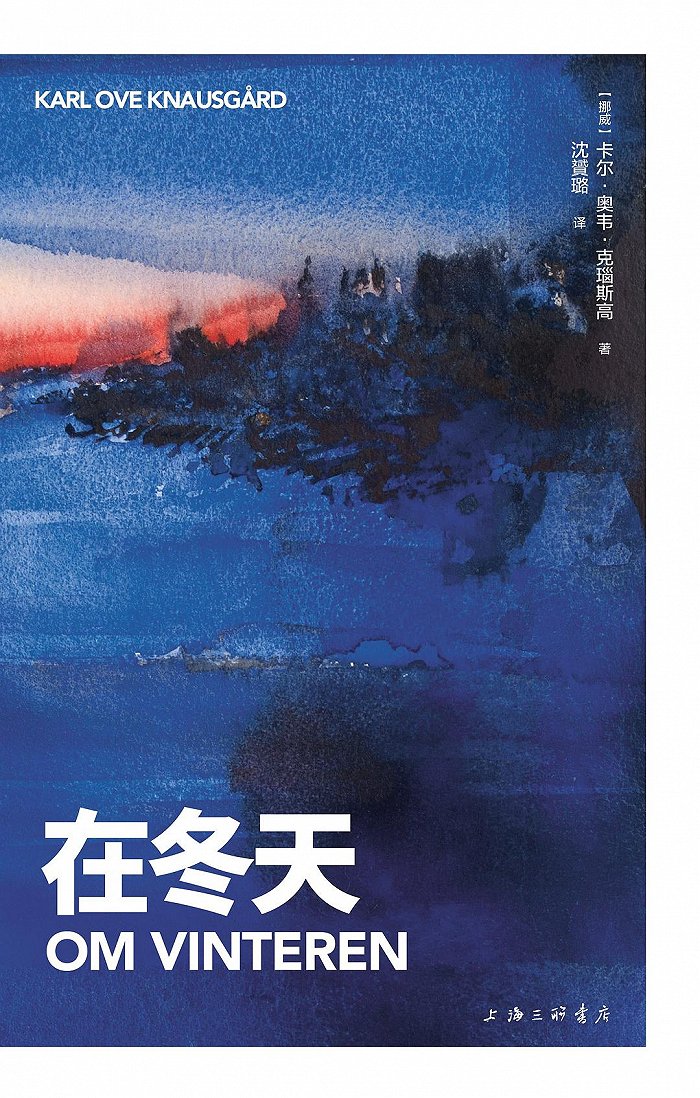
*(photo:JieMian)当第一批高升爆竹开始爆破,在傍晚早些时候的住宅区里噼啪作响时,他只是摇了摇头,坐在椅子上,不像我和我哥哥会冲到窗前去看—一定是路边拐角处的邻居,他没有耐心,等不及,不知道应该怎么做。当时钟接近十二点,一只又一只的爆竹从不同的地点蹿到天空上围着我们,父亲会清醒地点评每一只爆竹,有时还会赞赏两句,“汉森放的这只爆竹挺好”,但有时候他会批评两句,如果正好是从花园里放的一整箱烟花,那感觉仿佛自己是供奉这些灿烂的烟花的仆人,配不上那么绚烂的画面似的。“真是浪费钱啊!”他可能会这么说。其他邻居可能只会放一两只爆竹,而且也不怎么壮观,然后就变得吝啬无趣。
这些事情都无时无刻地不在暗示着,只有他,或者说通过他,我们家的人清楚地知晓应该怎么放鞭炮,既不夸张也不低调,既不浪费也不吝啬,而是会成功地放出完美的鞭炮,其他家庭很快就会目睹我们家的鞭炮,然后赞赏地点头。父亲会提前先布置好晾衣架的位置,那东西可以用作大鞭炮的电池,周围会放一些瓶子,然后小烟花就会从瓶子里升起来。我从没在其他时候见过父亲像放鞭炮时那么快乐的神情,他一只手握着打火机,另一只手挡着引信,然后突然站起来向我们小跑几步路—通常他从不奔跑—我从没见过在引信烧到火药,爆竹飞起来时,父亲的眼里发出的那种光芒。先是小的烟花,大概在十二点敲响前的二十秒钟左右,慢慢蔓延爬升到最大的烟花,用巨大的雷神为它加冕,一只形似蝴蝶的巨大生物在住宅区的上空中划过,就好像标志着一年的结束和新一年的开始。或许因为我们的烟花被其他烟花的发射给吞没了,没有人赞扬或是批评这份特别的烟花,但这无关紧要,因为一年中的这二十分钟充满了快乐和力量,毫无疑问的是,烟花的图像画在我们的头顶,画在这个世界之上的一个世界里,这被美丽和财富所堆叠的时刻并不是幻觉,它代表了一个真实的讯息,原来我们的生活也可以如此绚丽。
乌格雷西奇:煤灰
煤灰是一个我出生后第一批学会的词,它就像妈妈、爸爸、面包与水一样自然。我们生活的地方是一个工业小镇,镇上有一家煤灰厂。父亲就是那家工厂的工人。油在当时也是一个很自然的词汇。离我们镇上不远,有一个油井,煤灰就是一种从油里出来的东西。
我们住的地方被称作新村(全名为工人新村),新村里的房子(包括我们家在内)在当时都以未来的现代工人之家的理念建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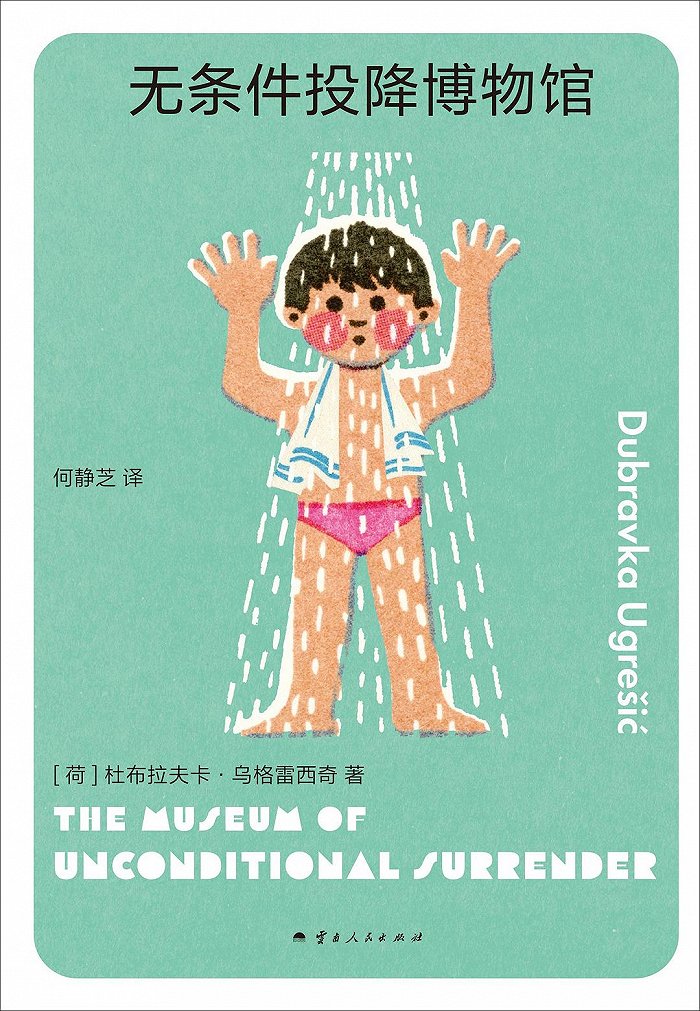
*(photo:JieMian)母亲常带我去煤厂的公共澡堂洗澡(这要比在家里点燃那台现代化热水器简单多了)。工人的睫毛上沾满煤灰,就像化了妆一样,眨起眼来好像玩偶娃娃。我记得我们在冷飕飕的石头隔间里洗热水淋浴,黑水如溪涧,向四面八方流淌,渗进灰色的肥皂水里。
母亲每天都与煤灰展开搏斗。早晨,她会用一块湿抹布擦窗台。
“又下灰了……”她会说,用食指,她最精准的测量仪器,抹一下窗玻璃,然后竖起食指,用居里夫人发现放射性物质时的语气,郑重其事地说,“看到没有?”
“看到了。”我盯着母亲沾满黑色油腻粉末的手指答道。
每天她都会打开窗户,看看外面,看看天,嫌弃地撇撇嘴,再把窗户关上。
“天上又有灰啦!”
煤灰,就像第五元素。
在灰色的日子里,天空仿佛飘洒毛毛细雨一般,持续飘洒着煤灰颗粒。在出太阳的日子里,空气中仿佛飘荡着金色的小蜘蛛。我常屏住呼吸,看它们静悄悄地、不可阻挡地侵入进来。当一粒这样的小蜘蛛落在我的手上,我就会将它碾碎,金色的它就会变成一个油腻腻的小黑点。
冬天,当天上下雪时,煤灰会连夜在积雪上铺开。早晨我们会抹去灰色的脏雪,激动地看着下面的洁白一片,玩造天使的游戏,即将我们小小的身体印在雪地上。
在我的记忆中,油这个词,总是跟铁托亲自这个表达联系在一起。有一年,某油井开幕,我们的主席铁托亲自到场。石油以惊人的力量喷向天空,在场所有来宾都被淋了一身。父亲专门为那次活动做的新衣服再也不能穿了。
“连翻个面儿穿都不可能了……”母亲伤心地说。
编者按:
童年时代,冬天的关键词有哪些?烟花?白雪?家庭生活?在挪威作家卡尔·奥韦·克瑙斯高的《在冬天》里,在克罗地亚裔荷兰作家杜布拉夫卡·乌格雷西奇的《无条件投降博物馆》里,两位作家写下了自己印象中的冬天。
同样是回忆童年的冬天,同样围绕着父母与家庭生活展开,他们呈现出了不同的情感:克瑙斯高“炫耀”起自家放烟火的技术,认为这正是比起邻居更高明的地方;乌格雷西奇描述煤灰落在积雪上的场景,孩子们先抹去雪上的黑灰,再将小小的身体印在白雪上。
有趣的是,他们也都透露了童年居住的环境。彼此差不多、生活集体共享是这两位作者的共同记忆点。克瑙斯高的小区由一长排相同的房子组成,乌格雷西奇的家则在工人新村,母亲会带着她去公共澡堂洗澡。那些关于烟花与煤灰的记忆,或许也与中国读者记忆中的童年相通。
克瑙斯高:烟花
我喜欢烟花,但不是那种限于地面或浮于地面的烟花,例如爆竹、圣诞拉炮、烟火棒、地面旋转式烟花、喷泉礼花这些,我对烟花的钟爱仅限于那种带引信点火装置的烟花,它能在高高的夜空中展现它的辉煌。从我记事起,我就一直喜欢这种烟花。小时候我在一个住宅区长大,也就是一长排相同房子的中间,里面有一样的车道,周围都是大小相同的花园,虽然每家每户发生的事情各不相同,但表面来看大家的生活都差不多。
最大的例外是新年夜,在午夜前后的几小时内,特别是在十二点前的最后几分钟和之后的几分钟里,所有孩子都会站在他们的母亲身旁,到花园里看父亲弯腰给爆竹的保险丝点火,直到保险丝着了火,父亲才会跑回来和其他人一起,站着看爆竹离开地面,升到空中,带着噼啪作响的花火飞到高空,不仅这一家子人能看到,甚至后墙外的人,以及所有其他住宅区的居民都能看到。烟花就这么每年一次地照亮了每个人心中真正的想法,也照出了每个人的真实身份。哎呀!这五彩缤纷的颜色,这绚丽夺目的光辉,不仅爆炸式地喷涌而出,还会悬在天上,再慢慢坠落,洒在漆黑的夜空中,告诉所有人它们的出处。至少在我父亲看来是这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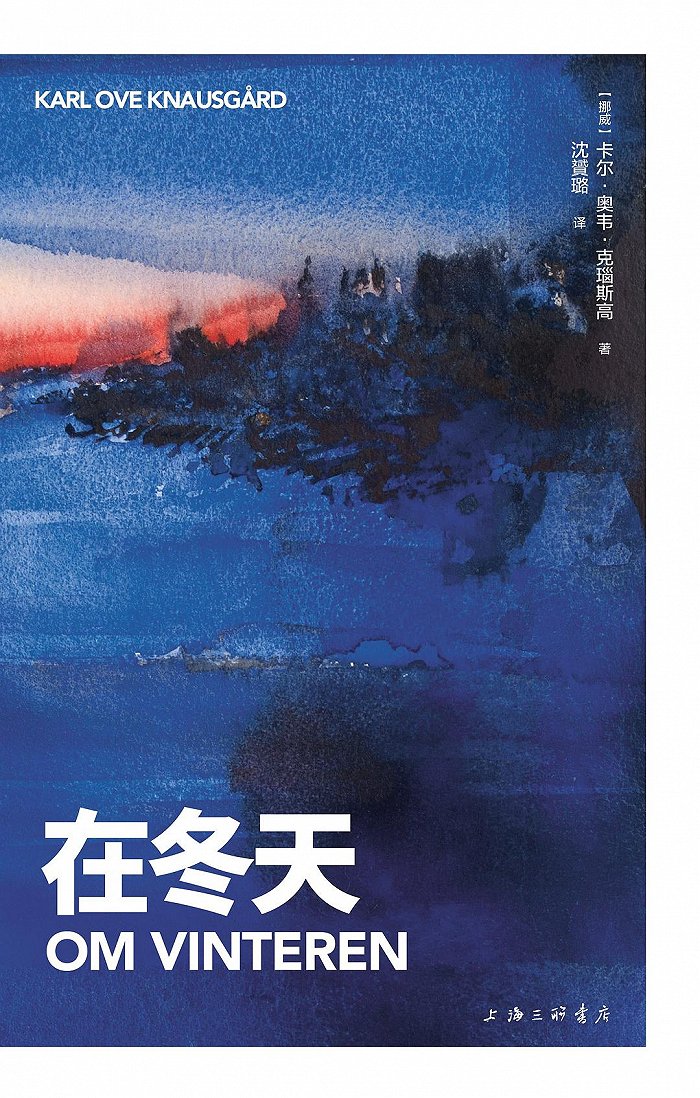
*(photo:JieMian)当第一批高升爆竹开始爆破,在傍晚早些时候的住宅区里噼啪作响时,他只是摇了摇头,坐在椅子上,不像我和我哥哥会冲到窗前去看—一定是路边拐角处的邻居,他没有耐心,等不及,不知道应该怎么做。当时钟接近十二点,一只又一只的爆竹从不同的地点蹿到天空上围着我们,父亲会清醒地点评每一只爆竹,有时还会赞赏两句,“汉森放的这只爆竹挺好”,但有时候他会批评两句,如果正好是从花园里放的一整箱烟花,那感觉仿佛自己是供奉这些灿烂的烟花的仆人,配不上那么绚烂的画面似的。“真是浪费钱啊!”他可能会这么说。其他邻居可能只会放一两只爆竹,而且也不怎么壮观,然后就变得吝啬无趣。
这些事情都无时无刻地不在暗示着,只有他,或者说通过他,我们家的人清楚地知晓应该怎么放鞭炮,既不夸张也不低调,既不浪费也不吝啬,而是会成功地放出完美的鞭炮,其他家庭很快就会目睹我们家的鞭炮,然后赞赏地点头。父亲会提前先布置好晾衣架的位置,那东西可以用作大鞭炮的电池,周围会放一些瓶子,然后小烟花就会从瓶子里升起来。我从没在其他时候见过父亲像放鞭炮时那么快乐的神情,他一只手握着打火机,另一只手挡着引信,然后突然站起来向我们小跑几步路—通常他从不奔跑—我从没见过在引信烧到火药,爆竹飞起来时,父亲的眼里发出的那种光芒。先是小的烟花,大概在十二点敲响前的二十秒钟左右,慢慢蔓延爬升到最大的烟花,用巨大的雷神为它加冕,一只形似蝴蝶的巨大生物在住宅区的上空中划过,就好像标志着一年的结束和新一年的开始。或许因为我们的烟花被其他烟花的发射给吞没了,没有人赞扬或是批评这份特别的烟花,但这无关紧要,因为一年中的这二十分钟充满了快乐和力量,毫无疑问的是,烟花的图像画在我们的头顶,画在这个世界之上的一个世界里,这被美丽和财富所堆叠的时刻并不是幻觉,它代表了一个真实的讯息,原来我们的生活也可以如此绚丽。
乌格雷西奇:煤灰
煤灰是一个我出生后第一批学会的词,它就像妈妈、爸爸、面包与水一样自然。我们生活的地方是一个工业小镇,镇上有一家煤灰厂。父亲就是那家工厂的工人。油在当时也是一个很自然的词汇。离我们镇上不远,有一个油井,煤灰就是一种从油里出来的东西。
我们住的地方被称作新村(全名为工人新村),新村里的房子(包括我们家在内)在当时都以未来的现代工人之家的理念建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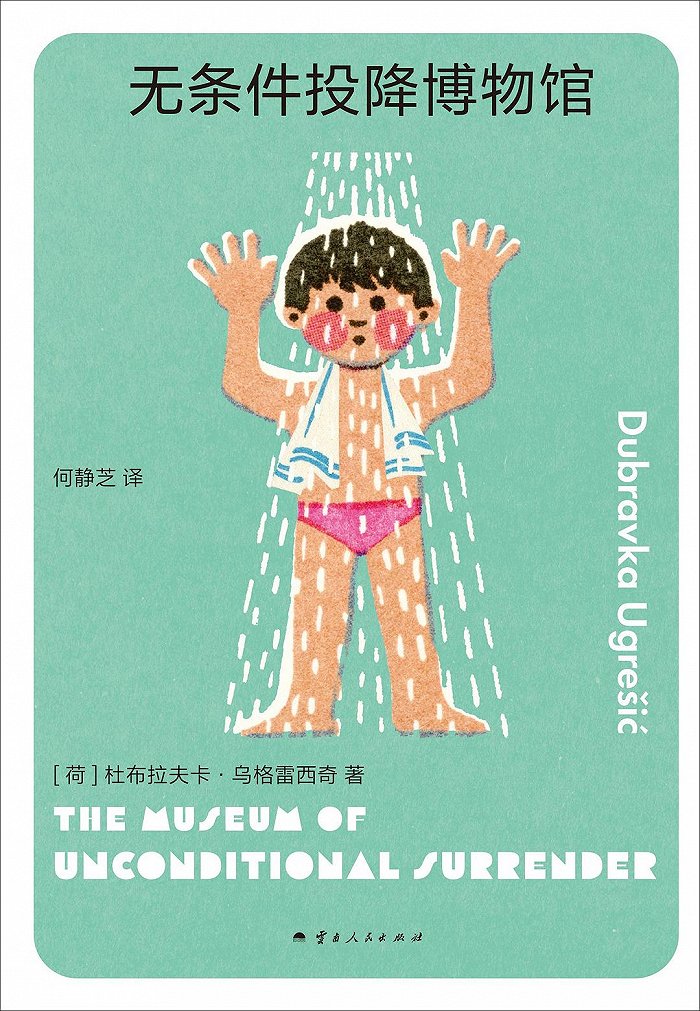
*(photo:JieMian)母亲常带我去煤厂的公共澡堂洗澡(这要比在家里点燃那台现代化热水器简单多了)。工人的睫毛上沾满煤灰,就像化了妆一样,眨起眼来好像玩偶娃娃。我记得我们在冷飕飕的石头隔间里洗热水淋浴,黑水如溪涧,向四面八方流淌,渗进灰色的肥皂水里。
母亲每天都与煤灰展开搏斗。早晨,她会用一块湿抹布擦窗台。
“又下灰了……”她会说,用食指,她最精准的测量仪器,抹一下窗玻璃,然后竖起食指,用居里夫人发现放射性物质时的语气,郑重其事地说,“看到没有?”
“看到了。”我盯着母亲沾满黑色油腻粉末的手指答道。
每天她都会打开窗户,看看外面,看看天,嫌弃地撇撇嘴,再把窗户关上。
“天上又有灰啦!”
煤灰,就像第五元素。
在灰色的日子里,天空仿佛飘洒毛毛细雨一般,持续飘洒着煤灰颗粒。在出太阳的日子里,空气中仿佛飘荡着金色的小蜘蛛。我常屏住呼吸,看它们静悄悄地、不可阻挡地侵入进来。当一粒这样的小蜘蛛落在我的手上,我就会将它碾碎,金色的它就会变成一个油腻腻的小黑点。
冬天,当天上下雪时,煤灰会连夜在积雪上铺开。早晨我们会抹去灰色的脏雪,激动地看着下面的洁白一片,玩造天使的游戏,即将我们小小的身体印在雪地上。
在我的记忆中,油这个词,总是跟铁托亲自这个表达联系在一起。有一年,某油井开幕,我们的主席铁托亲自到场。石油以惊人的力量喷向天空,在场所有来宾都被淋了一身。父亲专门为那次活动做的新衣服再也不能穿了。
“连翻个面儿穿都不可能了……”母亲伤心地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