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是工作,而是腐烂” | 卡夫卡逝世百年
-

奥地利著名作家弗兰岑·卡夫卡奥地利著名作家弗兰岑·卡夫卡(photo:JieMian)界面新闻记者 | 董子琪界面新闻编辑 | 黄月
“我不是爱斯基摩人,我和大多数人一样,生活在一个奇冷无比的世界,而我们既没有爱斯基摩人的生活基础,也没有他们的裘皮大衣和其他为生存而必备的辅助手段。和他们相比,我们大家都是赤身裸体的。……今天穿得最暖和的只有那些穿着羊皮的狼。他们日子很好过。他们的衣服正合适。”
《卡夫卡口述》记录了捷克作家古斯塔夫·雅诺施与卡夫卡的一次对话。卡夫卡说,在奇冷无比的世界中,他宁愿选择舒适冰冷的荒漠,而不是暖和的裘皮大衣。
一百年前的今天,奥地利著名作家弗兰岑·卡夫卡逝世。他生于1883年,生前曾出版《观察》《变形记》《乡村医生》以及《饥饿艺术家》四本短篇小说,留下三部未完成的长篇《失踪者》《诉讼》与《城堡》,为20世纪文学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1906年,卡夫卡获得法学博士。在波西米亚王国国营工人事故事务所,他成为了一个完美的职员。他是预防事故的专家,责任是检查和解释工业事故。他查看手和手指是如何卷到机器中的,研究创伤,明白身体创伤与心理状态之间的关系。卡夫卡的职业生涯顺利,稳步晋升。上司对他的评价是:具有非凡的天才,而且尽忠职守。
卡夫卡曾写过论述建筑业和建筑副业的保险、汽车保险还有刨床保护措施的公文,他为劳工工伤保险公司进行改革所写的专题报告至今仍保存在该公司。他曾将自己的公文郑重地寄给恋人和朋友。卡夫卡的公文,因富有逻辑性、专业知识精准、论证准确,受到好评。就像传记所叙述的,公文本身也象征着官僚体制的信心,一种对于正规的、有效组织的机构的信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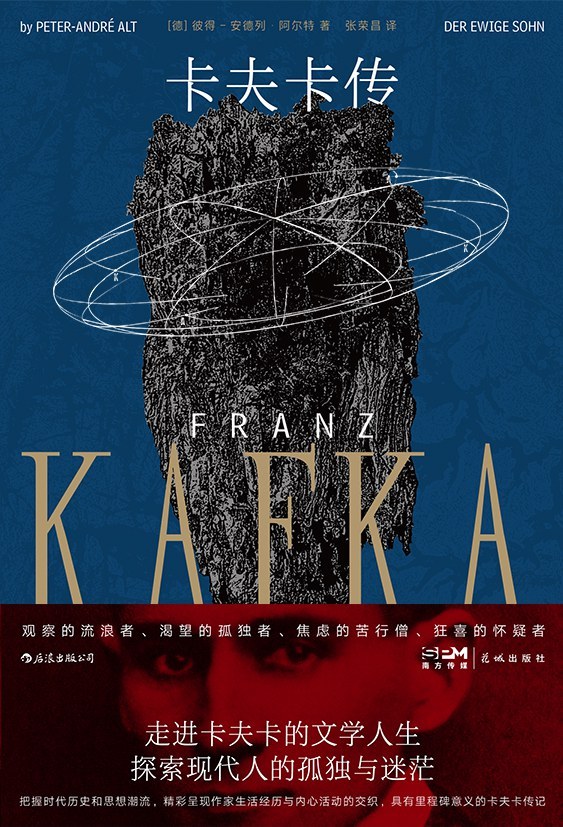
*(photo:JieMian)这份职业是他维持生计的保证。如他的家庭一样,职业为他提供了他所需的“结构”,然而是一种为了背叛的结构。卡夫卡常常由于神经质和疲倦而请假休息,但他通常不是由于工作而精疲力竭的。他每天从位于尼克拉斯街道的家庭公寓步行几个街区来到单位,8点上班,下午2点下班,午间有相当长的休息时间。工作可以让他逃避家庭。但办公室和同事关系对他来说都具有压力,他觉得办公室像是一间“黏糊糊的蜂房”。当同事问起他的身体状况时,卡夫卡会平静地回应“谢谢,我很好”,私下却认为这是一种欺骗。因为这种问候在他看来,就像一个苹果对另一个苹果发问,“那些蛰了您,爬进您体内的虫子怎么样了?”不过,与年轻的朋友聊天让他愉快,因为这是在“偷窃”属于保险公司的时间。
卡夫卡对工作和公文的意义表示怀疑,“这不是工作,而是腐烂,”他对年轻的朋友说,坐在办公室里,翻阅各种案卷资料,摆出庄重严肃的神态,只是为了掩盖对整个工伤保险公司的反感:“每一种真正积极的、目光明确的,使一个人感到充实的生活都具有火一样奋发向上的劲头和光彩。而我在做什么?我坐在办公室里。这个冒着臭气的、折磨人的工场。”
研读法律有时让他厌倦,因为对立法者而言,“人类除了罪犯就是胆小鬼,行为只取决于暴力威胁和恐惧。”他认为这是短视而危险的,创造的混乱大过于秩序。他亦觉察到工作与意义之间的脱节,工伤保险公司本是工人运动的结果,充满进步的光明精神。现实情况是,它变成了“文牍主义的黑窝”。
卡夫卡的日记透露了他对公文的真实情感。某次斟酌公文的结尾用语时,他产生了一种奇异的恶心感——仿佛口中含着一块生肉,“一块从他身体上割下来的肉”,不想吐出。相应地,他对出书的渴望也像是见到一家肉铺橱柜里堆满了肉的愉悦,“就好像这种渴求源自胃”。
一方面,割下来的肉和源自胃的渴求,都是与进食有关的比喻。有传记注意到了卡夫卡的进食问题与写作间的关系——卡夫卡后来成为一位素食主义者,是否与祖父曾经营肉铺、身为屠夫有关?卡夫卡曾以一种混杂着厌恶、讽刺与钦佩的情感回忆说,他不必吃祖父屠宰的这么多的肉。
《饥饿艺术家》更为直接地体现了关于进食与饥饿的焦虑。这篇小说讲述的是马戏团中的饥饿艺术家的故事,饥饿艺术家是一个待在笼中不吃不喝的演员,他的看守员通常都是屠夫。“他身着黑色紧身衣、脸色异常苍白、全身瘦骨嶙峋,席地坐在笼子里的干草上……他还把胳膊伸出栅栏,让人摸一摸。”当人们不再对这种艺术形式感兴趣的时候,他们就抛弃了仍然在笼子里忍饥挨饿的艺术家,在他死后,一头豹子进入了这个已经腾空的笼子。《变形记》中也有吃喝的对比:房客们大口大口吃着土豆烧肉,变成甲虫的旅行推销员格里高尔·萨姆沙在自己的房间听着咀嚼的声音,越来越没有胃口吃东西。饥饿艺术家与格里高尔的问题,也许就是卡夫卡自身的问题:这类人物仿佛患有某种厌食症,正因如此,他们才无法控制自己的身体。

*(photo:JieMian)另一方面,办公室如“黏糊糊的蜂房”、身体像“爬进虫子的苹果”,这些感受也让人不禁联想到《变形记》。人变成了甲虫,证明他真的改变了地位,还是他在现实中始终如此?或者说,在变成甲虫之前,格里高尔已然经受了类似的精神蜕变,他的自我早已解体。
卡夫卡将这个故事形容为“恶心的”。变为甲虫的意象在他最早的作品《乡间的婚礼筹备》中就已经出现:主角躺在床上时,相信自己具有一只大甲虫、一只鹿角虫或者一只金龟子的形态。他甚至可以做出冬眠的样子,把细腿贴在鼓起的肚子上。细腿和大肚子也是格里高尔的甲虫特征,卡夫卡对甲虫幻想的形容怪异而具体,可是却对出版社交代,不想要在书的封面上看到甲虫的形象。对此,传记作者推测,因为这一幻想来自于半梦半醒的状态中,精确的插图会使其丧失震撼力。
《变形记》中的甲虫之死,也让人想到人们在压死虫子时使用的暴力。在与年轻的朋友观察了某次布拉格的游行之后,卡夫卡批评政客:他们会冲着记者大家镜头微笑,却像践踏“讨厌的昆虫”一样,从千百万人身上践踏过去,只是无人在意。卡夫卡在1919年致父亲的信中,同样将孩子对父权权威的微弱反抗比喻为“虫豸的斗争”,虫豸不仅蜇人,而且以吸血维持自己的生存。
卡夫卡与父亲关系的紧张已经被多次论述过。《变形记》之前,卡夫卡第一篇发表的重要作品《判决》即表现了儿子与父亲之间的残酷斗争。 现实生活中,工作后的卡夫卡也仍与父母和三个妹妹同住。1907-1910年的三年多时间里,他睡在起居室与父母卧室之间的过道间里。这样的环境也让他对嘈杂的声音越来越有过敏性的反应,他讨厌留声机和电话,也曾在小说中描述过这种恐惧。长篇作品《诉讼》中,K拐进近郊一条小街,这时他突然听到了令人恼火的现代世界的嘈杂声,一台留声机叽叽嘎嘎地唱了起来。在文字与声音之间,卡夫卡更倾向于前者,因为父亲赫尔曼·卡夫卡的大嗓门和留声机、电话一样,都是对于写作与宁静的威胁,且更具有不容分辨的权威性。
《卡夫卡》[美]桑德尔·吉尔曼 北京大学出版社
《卡夫卡传》[德]彼得-安德列·阿尔特 花城出版社
《卡夫卡口述》[奥]卡夫卡口述 雅诺施记录 赵登荣译 上海三联书店
《卡夫卡小说选》[奥]卡夫卡 人民文学出版社
界面新闻记者 | 董子琪界面新闻编辑 | 黄月
“我不是爱斯基摩人,我和大多数人一样,生活在一个奇冷无比的世界,而我们既没有爱斯基摩人的生活基础,也没有他们的裘皮大衣和其他为生存而必备的辅助手段。和他们相比,我们大家都是赤身裸体的。……今天穿得最暖和的只有那些穿着羊皮的狼。他们日子很好过。他们的衣服正合适。”
《卡夫卡口述》记录了捷克作家古斯塔夫·雅诺施与卡夫卡的一次对话。卡夫卡说,在奇冷无比的世界中,他宁愿选择舒适冰冷的荒漠,而不是暖和的裘皮大衣。
一百年前的今天,奥地利著名作家弗兰岑·卡夫卡逝世。他生于1883年,生前曾出版《观察》《变形记》《乡村医生》以及《饥饿艺术家》四本短篇小说,留下三部未完成的长篇《失踪者》《诉讼》与《城堡》,为20世纪文学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1906年,卡夫卡获得法学博士。在波西米亚王国国营工人事故事务所,他成为了一个完美的职员。他是预防事故的专家,责任是检查和解释工业事故。他查看手和手指是如何卷到机器中的,研究创伤,明白身体创伤与心理状态之间的关系。卡夫卡的职业生涯顺利,稳步晋升。上司对他的评价是:具有非凡的天才,而且尽忠职守。
卡夫卡曾写过论述建筑业和建筑副业的保险、汽车保险还有刨床保护措施的公文,他为劳工工伤保险公司进行改革所写的专题报告至今仍保存在该公司。他曾将自己的公文郑重地寄给恋人和朋友。卡夫卡的公文,因富有逻辑性、专业知识精准、论证准确,受到好评。就像传记所叙述的,公文本身也象征着官僚体制的信心,一种对于正规的、有效组织的机构的信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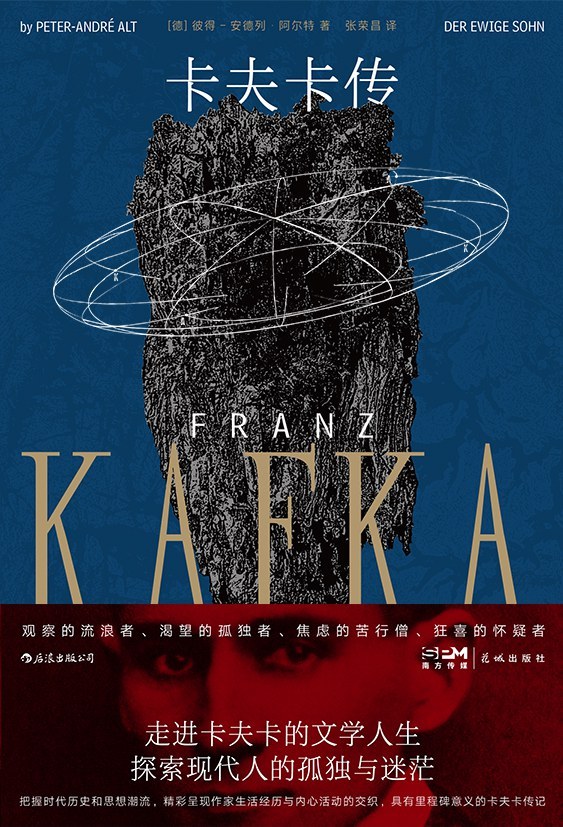
*(photo:JieMian)这份职业是他维持生计的保证。如他的家庭一样,职业为他提供了他所需的“结构”,然而是一种为了背叛的结构。卡夫卡常常由于神经质和疲倦而请假休息,但他通常不是由于工作而精疲力竭的。他每天从位于尼克拉斯街道的家庭公寓步行几个街区来到单位,8点上班,下午2点下班,午间有相当长的休息时间。工作可以让他逃避家庭。但办公室和同事关系对他来说都具有压力,他觉得办公室像是一间“黏糊糊的蜂房”。当同事问起他的身体状况时,卡夫卡会平静地回应“谢谢,我很好”,私下却认为这是一种欺骗。因为这种问候在他看来,就像一个苹果对另一个苹果发问,“那些蛰了您,爬进您体内的虫子怎么样了?”不过,与年轻的朋友聊天让他愉快,因为这是在“偷窃”属于保险公司的时间。
卡夫卡对工作和公文的意义表示怀疑,“这不是工作,而是腐烂,”他对年轻的朋友说,坐在办公室里,翻阅各种案卷资料,摆出庄重严肃的神态,只是为了掩盖对整个工伤保险公司的反感:“每一种真正积极的、目光明确的,使一个人感到充实的生活都具有火一样奋发向上的劲头和光彩。而我在做什么?我坐在办公室里。这个冒着臭气的、折磨人的工场。”
研读法律有时让他厌倦,因为对立法者而言,“人类除了罪犯就是胆小鬼,行为只取决于暴力威胁和恐惧。”他认为这是短视而危险的,创造的混乱大过于秩序。他亦觉察到工作与意义之间的脱节,工伤保险公司本是工人运动的结果,充满进步的光明精神。现实情况是,它变成了“文牍主义的黑窝”。
卡夫卡的日记透露了他对公文的真实情感。某次斟酌公文的结尾用语时,他产生了一种奇异的恶心感——仿佛口中含着一块生肉,“一块从他身体上割下来的肉”,不想吐出。相应地,他对出书的渴望也像是见到一家肉铺橱柜里堆满了肉的愉悦,“就好像这种渴求源自胃”。
一方面,割下来的肉和源自胃的渴求,都是与进食有关的比喻。有传记注意到了卡夫卡的进食问题与写作间的关系——卡夫卡后来成为一位素食主义者,是否与祖父曾经营肉铺、身为屠夫有关?卡夫卡曾以一种混杂着厌恶、讽刺与钦佩的情感回忆说,他不必吃祖父屠宰的这么多的肉。
《饥饿艺术家》更为直接地体现了关于进食与饥饿的焦虑。这篇小说讲述的是马戏团中的饥饿艺术家的故事,饥饿艺术家是一个待在笼中不吃不喝的演员,他的看守员通常都是屠夫。“他身着黑色紧身衣、脸色异常苍白、全身瘦骨嶙峋,席地坐在笼子里的干草上……他还把胳膊伸出栅栏,让人摸一摸。”当人们不再对这种艺术形式感兴趣的时候,他们就抛弃了仍然在笼子里忍饥挨饿的艺术家,在他死后,一头豹子进入了这个已经腾空的笼子。《变形记》中也有吃喝的对比:房客们大口大口吃着土豆烧肉,变成甲虫的旅行推销员格里高尔·萨姆沙在自己的房间听着咀嚼的声音,越来越没有胃口吃东西。饥饿艺术家与格里高尔的问题,也许就是卡夫卡自身的问题:这类人物仿佛患有某种厌食症,正因如此,他们才无法控制自己的身体。

*(photo:JieMian)另一方面,办公室如“黏糊糊的蜂房”、身体像“爬进虫子的苹果”,这些感受也让人不禁联想到《变形记》。人变成了甲虫,证明他真的改变了地位,还是他在现实中始终如此?或者说,在变成甲虫之前,格里高尔已然经受了类似的精神蜕变,他的自我早已解体。
卡夫卡将这个故事形容为“恶心的”。变为甲虫的意象在他最早的作品《乡间的婚礼筹备》中就已经出现:主角躺在床上时,相信自己具有一只大甲虫、一只鹿角虫或者一只金龟子的形态。他甚至可以做出冬眠的样子,把细腿贴在鼓起的肚子上。细腿和大肚子也是格里高尔的甲虫特征,卡夫卡对甲虫幻想的形容怪异而具体,可是却对出版社交代,不想要在书的封面上看到甲虫的形象。对此,传记作者推测,因为这一幻想来自于半梦半醒的状态中,精确的插图会使其丧失震撼力。
《变形记》中的甲虫之死,也让人想到人们在压死虫子时使用的暴力。在与年轻的朋友观察了某次布拉格的游行之后,卡夫卡批评政客:他们会冲着记者大家镜头微笑,却像践踏“讨厌的昆虫”一样,从千百万人身上践踏过去,只是无人在意。卡夫卡在1919年致父亲的信中,同样将孩子对父权权威的微弱反抗比喻为“虫豸的斗争”,虫豸不仅蜇人,而且以吸血维持自己的生存。
卡夫卡与父亲关系的紧张已经被多次论述过。《变形记》之前,卡夫卡第一篇发表的重要作品《判决》即表现了儿子与父亲之间的残酷斗争。 现实生活中,工作后的卡夫卡也仍与父母和三个妹妹同住。1907-1910年的三年多时间里,他睡在起居室与父母卧室之间的过道间里。这样的环境也让他对嘈杂的声音越来越有过敏性的反应,他讨厌留声机和电话,也曾在小说中描述过这种恐惧。长篇作品《诉讼》中,K拐进近郊一条小街,这时他突然听到了令人恼火的现代世界的嘈杂声,一台留声机叽叽嘎嘎地唱了起来。在文字与声音之间,卡夫卡更倾向于前者,因为父亲赫尔曼·卡夫卡的大嗓门和留声机、电话一样,都是对于写作与宁静的威胁,且更具有不容分辨的权威性。
《卡夫卡》[美]桑德尔·吉尔曼 北京大学出版社
《卡夫卡传》[德]彼得-安德列·阿尔特 花城出版社
《卡夫卡口述》[奥]卡夫卡口述 雅诺施记录 赵登荣译 上海三联书店
《卡夫卡小说选》[奥]卡夫卡 人民文学出版社








